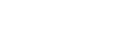石鲁像
我们是打外围站!
列宁曾讲过一段话,一时我找不到它的出处,只记得那段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一旦骑上脱缰烈马,就会产生这样的信念――即他必须保持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否则就会从马上摔下来。
石鲁既然立下了宏图誓言,那就毫无疑问地要坚定不移地走到底,他要投入全部的精力探索中国画的创新问题。
经过认真地分析、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不应该是水墨加素描。所谓“洋为中用”是吸收其优秀因素来营养自己,而不是被西化技法所同化,那样的混血儿是不伦不类的。中、西绘画各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以西画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画,以外来的素描人物标准来衡量中国画的人物画,或仅以透视、解剖、明暗的自然科学规律做根据来否定中国画,则必然会出现以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的主张,这样就显得片面了,等于忘记了我们还有自己民族艺术的规律,忘记了自然科学规律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艺术科学规律!客观地讲,它们各有各的优越性,也各有各的局限性,谁也不能代替谁,谁也不应该代替谁,二者之间不是什么继承关系,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借鉴的关系。石鲁坚持认为中国人物画必须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纳入中国民族艺术的体系。当然,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不足了。中国人物画在隋唐鼎盛,元明清渐趋衰微,以隋唐的人物画来说,主要是为佛事和帝王贵族生活服务,流派虽多,但都有一定局限,至于在写意人物画方面,现存有能看到的就更微乎其微了。仅从这些遗产中,何者能为今日所用,何者不能为今日所用,这都需要在不断地创作实践中加以解决。
石鲁立志要创造出足以表现今天现实生活的具有中国风貌的人物画表现方法。他酝酿了不少表现革命斗争的重大题材,但囿于一时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故暂且搁置,没有急于着手制作。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把大量的艰辛劳动投入山水及少量花鸟画创作中,遭到一些同行的误解和不满,认为他不搞重大题材,不重视人物画的创作,转向山水花鸟画了。石鲁坚决批驳了那种“题材决定论”,并说:“我们是打外围站!”他认为山水花鸟画中有非常丰实的技法经验可以作为创造新的国画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他之所以在这方面花费大量心血,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物画的问题,那才是他的主攻目标。
在这段时间里,他钻研了古代画论,要在汗牛充栋的论著里,找出所能汲取的东西,他遍临宋、元、明、清画迹。龚半千、石涛、八大、虚谷、吴昌硕诸家的作品他都进行过悉心研究。有一次,他临摹一幅宋人山水画,把一幅不足一方尺大小的印刷品,放大到六尺宣纸上,不仅严格地按比例放大,画了铅笔稿,还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原画的每一处细部,当时在一旁的方济众忍不住插嘴说:“你画的笔触是否太粗了一些。”石鲁答道:“比原画放大十几倍,笔触细了能立的起来吗?”方济众顿时为他的严格认真肃然起敬。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后也成了“长安画派”的集体创作作风。
不仅仅在山水花鸟方面,像真、行、草、隶、篆各类书体他均涉猎,他临过《祀三公山碑》,他临过金文,篆书《书法之道无穷》《景行再高道大语史》等巨制条幅,他融颜体、瘦金书、魏碑于一炉,几进几出,取古人之法为我所用。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人物画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当然,石鲁的努力也绝不只限于传统方面,如果认为他“排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曾说:“中国画,在题材内容上要新,要有时代精神,不能老停留在古人所表现过的一套里。在形式上,也要不断创新,要有时代的面貌特征。如何创新是个复杂问题,不能整天闭门苦思冥想,要到生活中去求新创新。另一方面,要广泛地去研究、分析、探讨世界各国、各民族美术发展的过去和现状,以创造发展我们民族自己新的艺术。”
石鲁曾为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去亲眼看看更多的国外美术原作而遗憾,但他仅凭接触到的国外美术印刷品,将风格、流派分门别类地归纳了一下,大概也不少于五百种。他感概地说:“如果你不了解世界美术的面貌,一味地去创什么新,什么风格,还自以为新,其实说不定是别人早就废弃了的旧玩意儿,不能坐井观天啊!更重要的是创新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里。”
他还谈到:“中国画在色彩表现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不如油画表现力强。国画不可能,也不必要向油画看齐。但可以吸收借鉴西方绘画,尤其是印度佛教绘画色彩上一些有用的东西。当务之急是要革新中国画的颜料。”
为此,他经常向学生们索要一些特殊颜料,并亲自一趟又一趟地跑到西安东关八仙庵一带的小地摊、小商贩那里,弄一些中国民间的品色、石色,拿回去一一进行试验。
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卓绝地做着别人很少去做的研究和探索,外围解决之后,离中心突破就不远了。
他突然扭转了主攻方向
进城以后,艺术创作上的条件与延安时代相比是天渊之别了。画家不必再为纸墨笔砚和各种颜料发愁,更不必由于条件的限制去专搞画板、木刻了。
石鲁摸索着画了一张油画,还下功夫创作了一幅表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农民在延安种西红柿的油画《七月的延安》。看来他好像是要放弃版画、国画把主攻方向指至西洋的油画了。
一九五四年,苏联油画展览在我国举行展出,油画热风靡一时,不少人更认为原来的猜测是毋庸置疑的了。
不料现实偏偏爆出了“冷门”。当石鲁参观过展览归来之后,在组织大家的座谈讨论发言中,却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他一反在全国已经卷起的油画热严肃地说:“我们必须搞民族自己的东西!”
他的不苟同时尚,突然扭转了人们所认为的主攻方向,震动着在座的每一位画家的心。
当时对中国画理论的认识是比较混乱的。不少人宣扬中国传统的东西是前进的“枷锁”,说它不科学,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主张以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而对传统的人物山水,花鸟画一概列入封建士大夫阶级文人画的另册,致使一个时期连杰出画家齐白石等人的声誉也一落千丈。
石鲁深刻地指出:“中国画并不是没有表现力,它和油画表现中很多原理是相同的。当前的问题主要是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他一再用鲁迅的话启发大家:即艺术愈有民族性,才愈有世界性。
应该说,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占领中国画阵地的。从此,他重整旗鼓,身体力行,开始了中国画的创作。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古长城外》。但是,他很快扬弃了那幅作品,他认为那幅画的创作方法过多地受了所谓“情节性”绘画的影响,说明得多而表现得少。此后,所谓“情节性”再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稍后,他创作的《瓦子街战役》《移山填谷》《云横秦岭》《渭华暴动》等作品,都着力于视觉形象的表现力。上世纪60年代的《东方欲晓》,特别是《转战陕北》,是他运用造型艺术表现力的最大成果,他采用了“比”、“兴”手法,以陕北浑厚、朴实、壮美的群山为背景,借景抒情。把领袖和人民、土地有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纪念碑雕塑般的庄重、雄伟,使人肃然起敬;又具有江山万里图般的壮阔、气势磅礴,使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忘怀。画家用热血般的朱墨书写了一部壮丽的革命史诗,是他在中国画创作探索中最富有形象表现力的不朽作品。
在印度万国博览会
一九五六年春天,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石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访问了印度。
所谓万国博览会,必然是众多国家竞争、宣传、激烈角逐的场所。各个国家纷纷将最能代表自己国色的艺术、文化、工农业产品陈列出来,刹时间,印度首都呈现出一派百花峥嵘、群芳斗艳的繁闹景象。新德里成了世界舆论瞩目的地方。
当时的美国、苏联竞相以光怪陆离的原子、核子工业显示力量,借此炫耀各自的大国优越地位。为了示其郑重,赫鲁晓夫亲自飞到了印度。
博览会中国馆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石鲁按照我国独特的传统进行了设计和布局。展览的内容有绘画、瓷器、刺绣、雕刻等手工艺品,还有土特产、纺织、新型机械设备等,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方面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印度各界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
有一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也来参观中国展览了。布尔加宁毕竟有以往的友谊,始终还亲切谦和,而赫鲁晓夫则截然不同,他盛气凌人,态度傲慢,时时摆出老大哥的样子。处处显露着不平等、不友好的卑劣神情。石鲁非常气愤,他对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的唯唯诺诺也窝了一肚子火,便以牙还牙地隔过老赫与布尔加宁握手问好,给赫鲁晓夫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过后,石鲁还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蠢猪,敢藐视我们中国,就得给他个颜色看看!”袁仲贤虽然不大高兴石鲁的过火举动,但却说不出任何指责的话来。
不久,石鲁与袁仲贤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那是在万国博览会即将闭馆的前夕,由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参观中国馆时,几次表示出特别喜爱中国的挂毯、地毯之类的工艺品,袁仲贤决定闭馆后将这一部分展品全部无代价的赠送给尼赫鲁。石鲁不干,说:“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八百万哪!”袁仲贤不以为然:“八百万也划得来,我们需要的是友谊!”石鲁愤怒起来:“中国人怎么这么没骨气?友谊难道是‘卑躬屈膝’吗?”袁仲贤也被激怒了:“石鲁,你说话要注意分寸,我作为大使,有全权处理这里的一切事情,你就不必多言了。”石鲁毫不退让地说:“你是有这个权力,但我们不能当败家子儿,你只要敢无限制地将东西送人,我就回国到党中央控告你!”“那就请便!”袁仲贤摆了摆手,两个人不欢而散。
夜深人静了,袁仲贤考虑再三,又来找石鲁,诚挚地谈到自己处理问题欠妥的地方,石鲁是个直肠子人,他一看大使同志主动找他推心置腹,便也立即检查了自己的急躁态度,错误偏差对于任何人都在所难免,关键是能够正视和纠正,他们促膝磋商,反复研究了适当的方案,斗争中的团结,使两个人更加亲近了。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
在印度的那段日子里,石鲁除去博览会的工作,抽空就到处去写生,他深入到新德里的各个角落,从广场集市乃至贫民窟。大堆小摞的写生手稿,记录着印度人民的详细生活。
十年浩劫之后,石鲁曾指着几幅残存的印度写生画稿,满怀深情地对人说:“这每幅画都有一个故事。”倘若碰上心情好的时候,他还能静静地讲上几个:
有一幅画,画着一个捕蛇人,枯瘦的身体,褴褛的衣衫,无声中道出了老人生活的艰辛,那犹如老树枝干的两臂双腿,坚硬而有力。他依靠捕蛇为生。印度不少地方多蛇,据说有一种毒蛇,只要人一看见,就必遭其害,而这老人恰恰是捕捉毒蛇的能手,他希望多碰到几只这样的毒蛇,一旦遭遇便可轻而易举的将它制服,拿到集市上多换几文维持最低生活的钱币。
石鲁对印度的妇女始终给予极大的尊敬和同情,他画过一幅“顶柴禾的女人”,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字,以深沉的笔调描写了印度妇女的头、手、脚。歌颂那亿万妇女的勤劳、磨难和忍耐。在新德里的街头,他碰到过一位抱孩子的印度少妇,她是个贱民。那极为低下的阶层中的妇女,身份就双倍的卑微了。她是从来不敢和高等人接触的,但是,当孩子手里拿着石鲁送给的中国桔子,那少妇向中国画家显露出难得的充满了感激而又带着苦涩的微笑,石鲁心里总还隐隐作疼,他的笔墨中正是饱含了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画家对印度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
还有一幅描绘印度古代寺庙的画,他画那张画时完全迷了进去,几乎画了一整天,直到天晚,大使馆的同志到处寻找,找到他时,他还沉漫在全神贯注的写生里。
有人说:时间是记忆的漂白剂。而石鲁在印度的短暂生活,无论是痛楚和欢乐,都久久清晰地留在他的大脑之中。
“我看这电影是送它一次葬礼!”
石鲁从印度回来,他所编剧的《暴风雨中的雄鹰》刚刚拍完,大家正等着他看样片,他应邀去了。电影放映中,他时时露出不悦的情绪,不等电影的结尾音乐停止,他就拂袖站起,忿忿离去。
据说这个电影的导演,当时刚从中国香港回来,对不少关键情节的处理,都非常谨慎,这使石鲁极不满意,他几乎是大声吼叫地说道:“要叫我导,我就不这样导!”
但平心而论,这个导演还是尽了相当大的努力,影片中几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如素有电影皇帝之称的金焰和在《平原游击队》中扮演李向阳的郭振清,以及后来在《吉鸿昌》中扮演霍金龙的白德彰,都各自通过真实的艺术表演,在《暴风雨中的雄鹰》一片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红军指挥员与藏族老人的感人形象,而且在电影放映之后,也获得了影剧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石鲁的反映则完全相反,当电影厂的同志撵到家来,征求他看过样片后的意见时,他不客气地说:“我看这电影,是送它一次葬礼!”他丝毫没有因为别人的赞誉而感到高兴,他的否定态度甚至有些不近情理。他认为有些人是闭着眼睛瞎吹乱捧。当然别人没有看过他的剧本原稿,他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剧情的原貌,他把一切恼怒都归结于导演身上,愤慨地说:“他改那一套我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又不接受!”他是那样痛恨对他剧本伤筋动骨的修改,以至于发话从此与那位导演断交!
诚然,一个画家一个作家爱自己的作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过于偏激固执不能说不是石鲁一个很大的缺陷,暴烈的脾气,急躁的性格,是这位卓越艺术家的致命弱点,有人说:“石鲁一辈子都在吃他脾气的亏。”这话品味起来,也许是有些道理的吧?!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