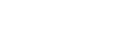工体往事: 一座球场的天真与伤感
1965年9月16日,北京。第二届全运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图/视觉中国)
从北京团结湖出发的43路公交车缓行通过三里屯,在接下来的路口拐了一个弯儿,进入南北向的道路。
这条路很容易地就将两侧区隔成迥然不同的世界。
左边是中国红街,楼宇间悬着一块块霓虹灯牌匾:火锅、烧肉、精酿啤酒……抵达此处的人目的纯粹——饱腹抑或买醉。
与之相比,满是尘土、砂石与噪声的道路右侧显得格外落寞。
除了戴着安全帽出入铁皮门的民工,只是偶有几个捂紧口罩的路人匆匆经过。
这是2020年7月到2022年年末时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样子。
在成为堆满脚手架的工地以前,这里也曾人声鼎沸,赶上球赛或演唱会,道路同样会被堵得水泄不通。
有司机打趣说,走这段路时,自己驾驶的更像是一艘小船,等人潮退去,才能漂走。
对许多北京人来说,建成于六十几年前的工体,远不只是一块运动场地。
它与周边的工人体育馆、游泳馆所组成的建筑群,更是承载了无数的集体记忆:1985年工体馆春晚、同年威猛乐队访华演出、1990年亚运会、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2009年北京国安夺冠……
如今回看,这些看似宏大叙事中的文体活动,像一个个索引,将人们带向了不同时代。
“看球,遛弯儿,怎么都成”
新中国成立以前,工体所在的位置是一座废弃窑厂。
展开全文
在彼时的北京版图上,这里隶属于东郊,在此处定居的人群庞杂无比,流民、商贩充斥其间。
与东西城的原住民相比,他们所处的环境恶劣得多,除了四处可见的窑坑,就是漫无边际的芦苇塘。
在那时,人们的基本生活尚不富足,遑论文艺、体育这些奢侈的爱好。
东郊命运转折点是在1955年。
那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工人体育展览会,会上,一位工作人员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和工会总主席赖若愚提了个建议:首都还没有大型体育场,希望日后能建成一个亚洲水平的体育场。
这一建议在四年后变成现实。
时值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
工人体育场便是其中之一。
35岁的建筑师欧阳骖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完成了这一场馆,其中囊括主赛场和室外篮球场、室外排球场、足球场、游泳场,以及人工湖。
在新中国建筑史上,工体的建造速度是位于前列的。
只用了11个月,这座体育场就在苇坑和荒土上拔地而起。
落成时,工体四周没有设置围栏,东、西两侧的大门上还赫然写着“自力更生”与“勤俭建国”。
成就这一建筑奇迹的是工人们。
一方面,该场地的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全国工人的工会会费;另一方面,工人加班加点地劳动,极大地提升了效率,提早赶完了工期。
为了表彰这一群体的功勋,体育场也因此得名。
从小到大一直住在团结湖的李翔今年33岁,他说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工人”的特定时代含义。
但他清晰地记得,幼时常去工体附近消磨时间。
带他去的人,是爷爷李有顺。
李有顺参与过工体的建设,每次和孙子来到这里,他都能讲出新的故事。
但听得多了,李翔发现,爷爷的陈述总是与艰苦有关,无非是每次都换了一个表达方式。
爷爷说过,东郊的地形条件很差,地面落差最大的地方有将近7米。
为找平地面,负责施工的队员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别人是拆东墙补西墙,他们是拆西土填东土”。
大概消耗了50万立方米的土,工体才得以开建。
建设时,工人没有趁手的设备,几乎全凭人力。
平整地面的工具大多是市政公司修路时淘汰的石碾,“几个人在头前拉,后面的人用原木柱子顶着,掌控方向”。
当时的工人们吃粮食需要粮票,对工人来说,固定的口粮很难让他们的肚皮撑到中午。
到了十来点钟,就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咕噜咕噜的叫声,纵使那样,活还是一点儿都没耽搁。
工体建成后不久,第一届全运会在其中举办。
这意味着,此前被排除在奥运会参赛国之外的中国,有能力参与和创办重大的体育赛事。
这块能容纳将近8万人的场地,也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展示给了世界。
在李有顺心里,参加全运会的目标显然过于遥远,但他与工体仍有一份联结——市工会组织的工厂联赛。
20世纪60年代,每至周末,他作为球员来这里参加比赛,“甭管输赢,每场球还能补助5毛钱”。
观战的市民络绎不绝,“家庭条件富裕些的,买6角一张的前台票,手里头稍微紧巴点,就花2毛钱上‘山顶’看,在哪儿都能看个乐子”。
于李有顺这种老一代人而言,工体是实实在在的让工人活动的场地。
业余时间,他们骑上单车,载着家人,紧赶慢赶地来到这里,踢场球,再嚎两嗓子,心里有再多的不痛快也都在此消散了。
2020年,李有顺听闻工体要翻修,特意又来了一趟。
看着眼前凌乱无序的施工现场,他跟孙子说,老辈的有些记忆,可能就跟着没了。
李翔许诺他,等建好了再带他过来,“看球,遛弯儿,怎么都成”。
但在去年年末,新工体竣工前夕,李有顺离世了。
1990年10月7日,北京。第11 届亚运会在工人体育场闭幕。(图/ 视觉中国)
“那场演唱会就像是做了一个梦,大家都舍不得从梦里醒过来”
在工体运行的前二十几年里,它的角色始终是球场。
直到1985年,一支摇滚乐队将文艺之风吹入了这片场地。
这支乐队是威猛乐队,当时的人们并不了解他们,对其所表演的摇滚乐更是知之甚少。
纵使这样,这场在工体馆的表演还是吸引了1.5万名观众。
前排的观众打着横幅,标语写道:“欢迎威猛乐团首次访华演出。”
人们手里握着的多是单位的赠票,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在门口的简易棚子中买的现场票。
谢秋霞曾是那场演出的观众中的一员。那年她25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彼时,她的叔叔从事外事工作,某次吃饭时,他偶然提及威猛乐队的消息。
心动的谢秋霞托叔叔弄到了一张票,然后她顺着人流,走进了场地。
在谢秋霞的回忆里,身边几乎都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人,“一开始,大家坐得都很规矩,但歌一唱起来,就有人跟着节奏晃起来了”。
乐队成员在台上一边唱歌,一边上蹿下跳。
远远地瞥到,谢秋霞有些不解,“没见过这种架势,有点儿吓傻了”。
但到了后面,拘束感变得越来越弱。
她和周遭的观众一样,一起打拍子,共同扭动身体。
那晚结束,谢秋霞得到了一盘磁带,磁带的A面是威猛乐队的原唱,背面则是歌手成方圆的中文翻唱。
从那往后,谢秋霞有了对音乐的评判标准,“一首好听的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人跟着节奏摇起来”。
尽管往后的日子,她没再去工体看过任何演唱会,但对她来说,威猛乐队的那次演出仍旧是她音乐方面的启蒙。
谢秋霞的女儿万芳在上中学时,偶然发现了家里橱柜上方的那盘磁带。
她听过后问妈妈:“您还听得懂摇滚呢?”谢
秋霞脸一黑,回她一句:“谁还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啊。”
这段对话发生的年份是2002年。
那一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国内因此举办了一些庆祝活动。
其中最为盛大的,就有GLAY乐队演唱会“ONE LOVE in 北京”。
GLAY是久负盛名的日本乐队,在世纪之交已经有了不少中国听众。
为了庆祝两国正常邦交和答谢乐迷,也为了杜绝“黄牛”炒票,他们在工体的这场演唱会采用了不售票的方式。
只要在规定日期内买一张价值50元的GLAY的专辑,再将里面的回执卡填好,寄回票务中心,就能够得到一张免费赠票。
买到专辑那天,万芳认真地填完了回执卡,并且再三确认了收票地址,她生怕因为小疏忽而错过这场演出。
好在不久后,她收到了赠票,然后她像多年以前的母亲那样,懵懵懂懂地进了工体。
只不过,这一次她进的场地,从工体馆变成了工体场,场地里的人数有3.5万人。
万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演出当天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GLAY乐队为现场观众特别准备了一首中文曲目《歌声与微笑》。
“乐手中文不好,唱出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是‘请把我的瓜,带回你的家’,整场人都在哄笑。”
第二件,是GLAY乐队在演出末尾时深情表露而说的那段话。
主唱TERU说:“我们相信,音乐可以创造奇迹。我们也相信,爱可以把所有的心连接在一起。下面,将爱的曲目献给大家,请听I’m in love。”
在“I'm just in love. I'm just in love. I'm just in love. Oh singin' my life”的歌声响起的那一霎,场地内的观众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人们一起挥手,歌唱,流泪。
演出结束后的10多分钟,没有人愿意离场,万芳说:“那场演唱会就像是做了一个梦,大家都舍不得从梦里醒过来。”
对歌迷而言,工体始终是那个最为包容的空间。
无论你所爱的歌手是何种曲风,也无论你身旁坐的是哪个人,只要踏入这个场地,就可以把一部分自我安放在这里。
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体在歌手心目中是个“朝圣之地”。
若想证明自己的实力,最佳方式无疑是登上场地中央的那方舞台。
2015年5月30日,北京。酒吧街上,一位女士坐在车上打电话。(图/ 视觉中国)
“上了球场,就得跟丫死磕”
对一座体育场来说,文艺活动更像“小径分岔的花园”,足球才是这块场地上恒常不变的主题。
有趣的是,有关足球的往事,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1981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坐镇工体,参加了世界杯外围赛,以3∶0的比分击溃来访的科威特队。
央视解说员宋世雄在直播时,高呼“容志行(进球球员名),祖国感谢你,人民感谢你”。
赛后,足球彻底点燃了人们的热情,满面荣光的球迷不住地欢呼,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走路,一边在长安街上行进,一边喊着“祖国万岁”,直到抵达庆祝的终点——天安门。
4年后,同是这块场地,狂喜转成了愤怒与暴力。
1985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被普遍看好的中国队,面对打平即可出线的局面,却在工体败给了中国香港队。
比赛结束,球迷卷起手中的旗帜,懊丧地走出了场地。
紧接着,“国足黑色‘5·19’”来了。
次年出版的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中如是写道:“看台上的观众也久久不愿离去,人们胸中堵着一股气,愤懑、失望、窝火、想不通、恨铁不成钢,所有的一切交织在一起,迸发出地动山摇般的吼声:‘曾雪麟,出来!’”“曾雪麟不能出来,否则他会被人撕成碎片,生吞活剥了的……汹涌的洪流冲出了工体,完全失控,至少两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被掀翻,暴怒的人流失去了理智,红了眼,变成一群可怕的野兽,见东西就砸。”
正是这次球迷的极端行为,让国内的体育爱好者意识到,球场上并无绝对的强弱之分,胜败乃是常事。
从那之后,北京的球场再未发生过类似事件,球迷群体也由此渐渐成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体又掀起一阵狂热——北京国安从先农坛迁址到此处,将工体作为球队主场。
尔后的二十几年,球迷们把工体当成了另外一个家。
比赛日的下午,方圆几公里之内,尽是穿着绿色球衣的忠实拥趸。
球场的门口形成了一条街市,围巾、手套、帽子,但凡想得到的周边产品,都能在此看见。
就连堵在路上的汽车车体上,也贴着球队的队标。
对他们来说,那是展现精气神儿的图腾。
开赛后,“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响彻24下看台(北京国安死忠球迷专属座位区)。
如果碰上的对手不是“善茬儿”,球迷还会用“京骂”招呼来客。
虽然做法有失体面,但屡试不爽的招数,常常让客队脚下一软,发挥失常。
作为铁杆儿球迷,刘海波就见证过很多次这样的胜利。
在他的小群体里,大家有个共识:“宁可让人踢死,也不能叫人吓死,上了球场,就得跟丫死磕。”
在刘海波的记忆里,最澎湃的看球体验发生在2009年。
那年,北京国安拿到了队史第一座中超冠军。
赛季临近结束,北京国安的球票越发难买。
每次主场比赛前,工体北路都有人支起帐篷,排着队,等待放票,“有的干脆一家老小全部出动,买票难度跟现在摇机动车号牌似的”。
当年10月的最后一天,工体座无虚席,战胜杭州绿城,北京国安即可斩获当季冠军。
队员不负众望,用4粒进球,为那个赛季画上了句号。
在16年的等待后,球迷终于可以把“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变成“我们是冠军”。
终场哨响,球员们走至场地中央,将主教练洪元硕抛至空中。
在忘情庆祝过后,素有“御林军”之称的北京国安队员们来到了场边,向球迷深深鞠躬,感谢他们的助威与呐喊。
刘海波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真的感觉球场就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起笑,一起哭。”
正是出于这种关系,球迷之间称工体为“北京最后的四合院”。
就像BTV足球解说嘉宾杨天婴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人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失去很多,会回忆很多,而这个球队将成为一个载体。人们回忆里失去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
2014年5月26日,北京。工体看台上的北京国安队球迷。(图/ 视觉中国)
夜晚的开始与结束
由于毗邻外交公寓和大使馆,工体是北京接受酒吧和俱乐部文化最早的地方之一。
千禧年前后,工体周边出现了许多娱乐和餐饮场所。
人们看完比赛,夜晚才正式宣告开始。
在球迷口中,赢球了得喝酒庆祝,输球了更要喝酒排解。
于是,工体北门的MIX与VICS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的两大去处。
刘海波很早就进过这两家俱乐部。
他说,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的酒吧没法比,屋里的空气比较难闻,地面也是黏糊糊的。
但这丝毫不耽误人们在里面纵情声色,街边不时有停下的超跑,从车上下来的人,一头便扎进店内,然后跟着Hip Hop音乐摇晃起来。
“对那时的人来说,一提到放松的好地方,最先想到的就是工体。”
为工体酒吧和夜店贡献收益最多的,往往是中年人。
在经济飞速增长的那几年,他们最舍得在这里花钱。
年轻时的刘海波见过很多“摆阔”的,有的服务生只是帮客人捶两下肩膀,拿一会儿衣服,就能收到一笔不菲的小费。
有一阵子,工体附近店面的服务生工资要比白领高出不少,很多人都闻讯来此,争取得到这份工作。
刘海波说:“那时的工体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野性,各个阶层的人都愿意在那多停留一阵儿,有钱的去夜店喝酒,兜比脸还干净的也能找到路边脏摊撸串,半夜的时候最有意思,大家喝多了酒,全都聚在马路边上,互相搂着,谈心的、20岁和50岁称兄道弟的,干什么的都有,等喝不动了,就招招手,有的是车能把人拉回家。”
对于那些居住地稍远的人来说,打车不是明智的选择。
为了节省这部分开销,他们往往会在这守候第一班出城的早班车。
公交车上载着满满当当的乘客,以老人居多,老年卡与刷卡机频繁发出的“嘀”声,常会让人诧异,这究竟是这座城市的正常状态,还是自己的酒劲未过。
与漫长的等待共同而至的,是人们对夜宵和早点的需求。
在买醉的人之间,最有声望的那家店叫做“老满太太”。
老太太经历颇为传奇,她是这个区域最早“练摊”的一批人之一,她所开发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熏鸡架、炒粉和鸡汤豆腐。
据说,她凭着这把手艺,给两个儿子在北京买了两套房。
等子女安顿好,老太太退居幕后,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日子。
故事的可靠性已无从而知,但老太太的商海传奇起码向人们昭彰了工体辉煌之际所产生的影响力。
现今,“老满太太”的店开在一路之隔的中国红街,店内很难寻到一丝一毫过往的痕迹。
它与周遭的连锁店面别无二致,尤其是在流程上:扫码点菜,快速出餐,然后再盼着客人能尽早离去,以便翻台招呼下一批慕名而来的“打卡”者。
和时代大潮的翻腾与沉浮不同,个体与区域的变化总是悄无声息地发生。
与“老满太太”一并离开街头的,是那些曾经叱咤的老牌夜店和酒吧。
加之疫情的重创,一家家店面挂上了“歇业”“转让”的牌子。
没人弄得清是年轻一代的审美趣味生变了,还是这种范式的夜生活已然不符合当下潮人的价值理念。
如今,在距离工体不远处的三里屯,总有背着配有昂贵镜头的单反相机的人出没,他们被人戏谑地称为“老法师”。
“老法师”们极力地捕捉着最前沿的诱惑与美艳,而在拍摄完毕行经工体之时,他们却很少想起,自己可以举起镜头,为这座城市最有标志性的建筑留下些许光影。
2020年,服役了一甲子的老工体在完成诸多使命后隐匿了。
2022年的跨年夜,翻新完成的新工体迎来了首秀。
晚会上,崔健奏唱着《一无所有》,沙宝亮高歌着《国安永远争第一》,齐秦用歌声讲述着《外面的世界》。
在不久后,北京国安队会回归这里,享受着拥有观众的比赛,歌手也依旧会期待在这扬名立万。
一切仿如还在昨日,一切又好像都得到了更新。
关于这座球场的故事,总有要被遗忘和抛舍的点滴,也总有要继续书写和镌刻的部分。
北京和工体的羁绊仍将在此延展,至于未来,也许会像1986年这座场地传出的那首歌《让世界充满爱》中所吟唱的那样:“一年又一年,我们拥有明天。”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