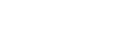柳五儿介绍
柳五儿,清代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柳嫂子之女,生得一副好模样。五儿和宝玉的丫鬟芳官是好朋友,芳官把宝玉喝剩的玫瑰露给了她,因母亲不慎得罪了司棋等人,被冠以贼名。幸亏平儿相助,她们母女的冤情得以洗清。后成了宝玉的丫环。
人物设定
袭黛玉之弱,秉晴雯之姿
《石头记》,典出《左传》“石言于魏榆”,隐含着以“顽石”发言“干涉朝政”的微辞;后改名为《红楼梦》,指其书写了“红楼闺阁梦一般的人生”,对干涉朝政的锋芒有所掩饰。自面世之日起,《红楼梦》就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长久的占
据着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把交椅,民间还广泛的流传着“开谈不说红楼梦,尽读诗书也枉然”的话语。
曹雪芹先生在悼红轩“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写就了“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书里塑造的一系列赚人热泪的人物形象,从高高在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千金小姐公子爷儿到身份低微,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丫鬟小厮,无一不浸淫着曹雪芹的心血。这些活在“石头城”里的人,大都“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丫鬟,可以说是《红楼梦》里沉默的大多数。有的“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终究因“风流灵巧招人怨”而多 “寿夭”;有的“枉自温柔和顺”,背地里向主子打着小报告,终究还是“优伶有福”罢了;有的因一句“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的玩笑之词就被骂为带坏爷儿的“下作小娼妇儿”,最后因羞愧难当而投井自尽……
柳五儿,也是众多丫鬟中的一个。她的初次亮相是在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而且,着墨并不多,只有看上去可有可无的寥寥数语:
“原来柳家的有个女孩儿,今年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儿。只是素有弱疾,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丫鬟,差轻人多,且又闻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
不过,这字数不多的几行字,已经表明了她将是一班丫鬟里不平凡的一个:
首先,这个出身并不高贵的“厨役之女”,并没有一丝的世俗之气,“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并不是那种井底之蛙的小丫鬟;
其次,她袭黛玉之弱,身子骨是柔弱的,“眉眼儿有点象你林妹妹”,是一副弱质纤纤的小姐模样;
再次,正是由她的“素有弱疾”才引出了昭示着大观园里奴婢丫鬟之间你挣我夺的“玫瑰露引出茯苓霜”,推动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还不是全部,柳五儿最不平凡的一处,还是她的秉晴雯之姿——容貌与心高气傲的晴雯就如同是一个模子引出来的。就连与晴雯有着千丝万屡联系的宝二爷看着“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儿,松松的挽着一个髻儿”的柳五儿,也觉得“居然是晴雯复生。”
在书里的第六十回,曹雪芹先生抛出一个与林黛玉同样柔弱与晴雯容貌相若的柳五儿出来,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巧合,而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袭黛玉之弱
在中国的历史卷册上,历朝历代对于美的定义都或多或少的有着些许的差异,一如唐朝人眼里的国色天香到了宋代也许就成了一个肥胖碍眼的东施。不过,古往今来,身子骨柔弱的女子,都无一例外的格外惹人心疼,轻易便挑起男子的保护欲,让所谓的文人雅士生出怜香惜玉之心。
柳五儿,正是那种似乎风吹一吹就倒的弱小女子。她的初次出场,就别有一番气派:
1、芳官为她讨要玫瑰露。不知玫瑰露是什么珍贵的补品,不过,那是万千宠爱集一身的宝二爷吃的东西,自然不会是什么寻常人家吃得的。只是用“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装着的“胭脂一般的汁子”,看起来如同“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不过,柳家的却欣喜的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是个尊贵物儿”, “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大情”。
2、姑妈家送茯苓霜。茯苓霜是“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的,在宁府当差的姑妈转送给柳家的,是因为“怪俊,雪白”的茯苓霜“正是外甥女儿才吃得的”,“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
茯苓霜与玫瑰露一样,都是主子们用以补身吃的,并不是一个奴婢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从后文可见,即使是身为少爷的贾环、半个主子的赵姨娘想吃也只能暗地里央求彩云去偷。不过,身子柔弱的柳五儿却因了种种原因吃着这些尊贵物儿。由是可以推测:
其一,柳五儿的身子一向柔弱,经常需要进补;
其二,这些细节也暗示着她不是一般的奴婢,虽是出身不好,吃穿用度与贾府的姑娘们却是近似的。
在登场亮相之后,柳五儿进怡红院当一个伏侍宝二爷的丫鬟之路一波三折,其中,大都是因其“怯弱有病”。此外,与黛玉相同的地方,还有两者都同样“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常常会“呜呜咽咽直哭一夜”。
当然,柳五儿所袭的只是黛玉之弱,并不是其神。出身是两者之间难以跨越的天堑,也决定着两人不同的命运。出身书香之族的林黛玉自小就为父母“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读过书,诗词歌赋自是不在话下。
反观柳五儿,应该也些须认得几个字,不过,贾府里的老祖宗对书也是不甚感冒,觉得姑娘们上学也不是在“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另外,“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当时大户人家奉行的金玉良言,贾府的大奶奶李纨、二奶奶王熙凤都不是什么知书之人,柳五儿,身为厨役之女,有如是的主子,自然也不会把时间花在读书识字上面。
即使是同样的体弱多病,个性行为也是截然不同的。由始至终,大观园里都只有一个“堪怜咏絮才”的“玉带林中挂”,与贾宝玉花下共读《西厢记》的林妹妹也只有一个。柳五儿虽是袭黛玉之弱,却是只有形似而非神似,没有潇湘妃子的才气,也没有她的“果然比别人又
是一样心肠”。
秉晴雯之姿
如果说柳五儿与林黛玉同样身子柔弱只是一种巧合,因为清代的审美眼光同样的以柔弱为美,“一个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正是不少千金小姐的真实写照。那么,秉晴雯之姿可以说是曹雪芹先生设计柳五儿这个人物时打出的另一张王牌。
柳五儿与晴雯同样是丫鬟,而且,顶着同一身的皮囊。在众人的眼里,两人不仅容貌上相似,骨子里也有着同样的“狐媚”,是带坏爷们的“祸水”。
“我见那孩子眉眼儿上头也不是个很安顿的。起先为宝玉房里的丫头狐狸似的,我撵了几个。”
“这里头就是五儿有些个狐媚子,听见说,他妈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说要讨出去给人家儿呢,但是这两天到底在这里呢。”
——以上分别是王夫人和袭人对成为了宝二奶奶的薛宝钗说的话,都是要她注意提防这种狐狸精一般的女子。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主子,一个是丫鬟里的头儿,两人对柳五儿的评价却是惊人的一致。
无独有偶,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里,王夫人受人挑拨将病中的晴雯大骂一通,不仅“看不上这浪样儿”和“轻狂样儿”,还将其称为“这样妖精似的东西”。
清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朝代,朝廷仍是以儒家思想治国,宋明理学依然影响深远。在当时的大户人家看来,丫鬟也好,姨娘也好,都得符合以下规则:“虽说是贤妻美妾,也要性情和善,举止沉重的更好些……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这是王夫人对贾母说的一番要求,其实,这几句话也间接断了诸如晴雯、柳五儿等狐媚女子成为姨娘的希望。
晴雯到了“抱屈夭风流”的时候才后悔——“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不是我说一口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目睹了晴雯惨况的柳五儿选择了抽身而退,趁早离开是非之地。造成她作出这个决定的,除去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王夫人的“标准”之外,还有宝玉态度的转变:“我想一个人,闻名不如见面。头里听着,二爷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亲再三的把我弄进来;岂知我近来了,尽心竭力的伏侍了几场病,如今病好了,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剩出来,这会子索性连正眼儿也不瞧了。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的贾宝玉不再是那个“候芳魂”的少爷,柳五儿也不会再有“承错爱”的机会了。
晴雯和柳五儿,虽然两人的容貌相近同样伏侍过贾宝玉同样被看成是“带坏爷们的狐媚女子”,但是,她们,绝对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晴雯,可以说是丫鬟中叛逆血液最浓重反抗最强烈的一个。她敢说敢做,毫不忌讳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不过,在你挣我夺的大观园里,也正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为她招来了灾祸。
至于柳五儿,她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也不敢得罪什么人,只想安安分分的尽本分。她与袭人有一处地方是相同的:都想着走奴婢->姨娘的路,进而成为半个主子。可惜,两人的希望都落空了:一个成为优伶的夫人,另一个配了出去,估计也是嫁给了一个小厮。
曹雪芹先生在柳五儿身上同时注入了林黛玉和晴雯的血液:前者是地位高贵的主子中的叛逆者,后者是身份低微的丫鬟中的叛逆者。不过,柳五儿空袭黛玉的“多愁多病身”,白秉晴雯的 “倾国倾城貌”,终究,还是一个沾有奴婢性格的人:
1、以伏侍主子为荣幸:千方百计想着到怡红院当一个伏侍宝二爷的丫鬟也是目的明确的:“趁如今挑上了,头宗,给我妈挣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二宗,我添了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三宗,我开开心,只怕这病就好了。就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
2、遭受不公的对待也是敢怒不敢言:第60回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一夜听着众媳妇的规劝、抱怨、奚落,她心内又气又委屈却只懂得“呜呜咽咽的直哭”。
3、面对身份地位上横亘的桥梁,不敢越雷池半步:第109回,她伺候宝玉“候芳魂”,宝玉“把他当作晴雯,只管爱惜起来”,她却是领悟不到,直说 “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袭人姐姐,都是仙人儿似的,只爱和别人混搅”“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么脸见人”
可以说,柳五儿也是当时一类型奴婢的代言人,她们也是天生丽质,不过,大都没有反抗的自觉性,或自觉或被迫的适应着那样不公的环境。生活在某个时代的人,就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对柳五儿,不能苛责什么,只能说4个字——“哀其不幸”。
毕竟,120回的《红楼梦》里只有一个林妹妹,只有一个晴雯,却有无数个柳五儿。
书中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朱一玄先生判断的依据。庚辰本《红楼梦》第77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你们又懒待出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你就成精鼓捣起来,调唆着宝玉无所不为。”芳官笑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王夫人笑道: “你还强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你连你干娘都欺倒了,岂止别人!”因喝命:“唤他干娘来领去,就赏他外头自寻个女婿去吧。把他的东西一概给他。”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们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一概不许留在园里,都令其各人干娘带出,自行聘嫁。一语传出,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都约齐与王夫人磕头领去。(注:程乙本缺少脂本中“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
朱先生说,从以上看到,王夫人等往皇陵上去时“柳五儿丫头短命死了”。他判断的前提是:那丫头=柳五儿,芳官调唆宝玉要丫头。但是,从柳五儿在那几回提到的描述看,确实是误读红楼了,这样说未免武断了。推理逻辑如下: 首先,王夫人等陪同贾母“往皇陵上去”是何时呢?查对脂批本: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贾母、邢、王、尤、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以后方回。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曰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第58回)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第64回)
由此可见,“往皇陵上去”期间是在第58~64回。那么,如果像朱先生理解的那样,在王夫人等“往皇陵上去”当口,丫头五儿就已经“短命死了”,那么在王夫人回来的那一回后,就不应该再出现丫头五儿的活动了。庚辰本文本是否如此呢?
经过核对,我们发现在第77回前,脂本最后一次出现柳五儿的是第70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的气病了的柳五儿: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 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 竟将诗社搁起。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顽笑。此前出现在第63回:宝玉点头,因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春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诉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欢。只是五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去又气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未免后悔长叹,因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芳官可说了没有。”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可见,柳五儿在王夫人等上皇陵后,柳五儿并没有死去!宝玉也还一再惦记着她的重病,丫头们还等者她回来进宝玉房里呢。
其次,既然柳五儿重病,是否就一定死去了呢?我们考察脂本前70回文本叙述,并无此征兆。第一次出现五儿名字处,在第21回: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我知道?你爱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 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声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伏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 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以后多次出现,重点故事是第60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玖瑰露引来茯苓霜》: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今年才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袭、紫、鸳皆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是五儿。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宝玉正在听见赵姨娘厮吵,心中自是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得等吵完了,打听着探春劝了他去后方从蘅芜苑回来,劝了芳官一阵,方大家安妥。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去罢。”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见瓶中亦不多,遂连瓶与了他。还有,第61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脏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报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倘或眼不见寻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以后提到的还有一次,第62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儿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
我们仔细察看文本描述,并没有发现五儿病死这样的迹象,最多是积劳积病。那么可以推论,以前朱先生等宣判柳五儿为死犯的铁案不铁了,是冤假错案。下面,我们要来探索“短命的丫头”真正为谁。
那么,王夫人口中的这个“教唆犯”——短命死了的丫头,究竟是哪位呢?我们可以重新考量一个目标。总体看来,我们要考察“短命死了的丫头”的身份,这个丫头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她必须是宝玉房里的,这样才能靠近宝玉,“调唆”宝玉去要“柳家的丫头五儿”; 二、她必须是宝玉很是在乎的一个贴身丫鬟,至少要像晴雯似的“磨牙”和“妖媚子”,于是才能游说宝玉的思想, “有资格”得到王夫人的“唾骂”;三、她必须是在王夫人等上皇陵后的章节中不再出现,包括任何故事情节,即在前面要有叙述,但在第58回—64回文本叙述期间开始蒸发了,以后叙述中永远消失。此外,还要满足一个充分条件:在第77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前,文本叙述的丫头中,只有一个消失的人选,即目标是唯一的,舍此无他。
考证背景
考证:看柳五儿之未死
近十数年,许多红学家们一直认为在脂批本上老太妃下葬期间的第58回开始到第64回上半部,柳五儿就业已悄悄“短命死了”,而在程本120回中,从第77回到第101回到第118回等,共计九回里都提到或重点安排故事情节。只有林语堂、周绍良等先生认为,第109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是原作,而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承认此回“较有精彩,可以仿佛原作的。”最早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里明确指出程本中后来五儿起死而复生,虽然承认“在情节的前后照应上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只是在性格上和前文
“没有相近之处”,判别为程乙本改写的。但是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发现这样遽然判断有失所察,值得商榷。
丫鬟考证
经过细密梳理,参看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中论述的庚辰本《红楼梦》四百多个人物,前77回消失的人物很多,譬如丫鬟,就有一个投井的金钏,还有故事情节,但她是王夫人房里的,不符合上列条件。
经查,宝玉房中在64回以后消失的丫鬟,庚辰本明文的有例举如下:
1、丫头靛儿:第30回出现了两次名字的“因找扇子”的靛儿,无归属人,朱先生因故事发生在贾母处,便列为贾母的丫头
2、丫头篆儿:第52回: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钻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唬的小丫头子篆儿忙进来问:“姑娘作什么。”
似乎是宝玉的丫头,但是第57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就明确否认了: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悄悄的递与莺儿。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 另有第62回为旁证: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丫头笑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可见,篆儿不是宝玉的丫头,是邢岫烟的丫头。
3、丫头紫绡:出现四次。不过,“紫绡”是在戚序本和蒙府本,而在庚辰本影印本底本上,原作第27、28回三个均有改为“紫娟”, 第64回作“春燕”。程本无“紫绡”,出现时为“秋纹”、“紫娟”和“春燕”。
4、丫头檀云:出现六次。第24回、34回、52回,还有诗词两次。国学论坛另外,程本上把贾母给宝玉的“珍珠”(后改名袭人)丫头换为原名“蕊珠”。
综合以上,真正符合以上所列条件的,统共只有丫头檀云和紫绡两个选项。那么文本描绘中,宝玉是否很在乎哪个贴身丫鬟呢?有故事情节为证否?因为紫绡真正出现提名的,也就是在戚序本和蒙府本,庚辰本只有两出,别的就没戏了。但是对于丫头檀云,似乎隐藏着与宝玉很亲密的故事,下面详细探究。
其实,几十年前就有人论述檀云和麝月一样有着丰富的故事了。最早论述的是周绍良先生和张爱玲女士,他们曾经论述《红楼梦》中有被删去的檀云的故事。并且,周先生在其《被删去的檀云的故事》中探佚说,有檀云焚香的故事。首先从第23回的《夏夜即事》说起: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水亭处处齐纨动,帘卷朱楼罢晚妆。——其中,麝月、檀云、琥珀、玻璃皆为宝玉的四个丫鬟,她们看来是各司其职了。
细究起来,和“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对应的,还有一处在第78回。清代读书人早也发现了,最早谈到檀云入诗的是大某山人姚燮(梅伯),他在第78回的《芙蓉诔》“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处,写到:“以二婢名入文,融化无迹。” 仔细考量诗句,不但如此,还有一部分故事蕴涵其中。周先生分析说,“窗明麝月开宫镜”是指第20回《王熙风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描写的内容:宝玉笑道:“咱两个作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早上你说头痒,这会子没什么事,我替你篦头罢。”麝月听了便道:“就是这样。”说着,将文具镜匣搬来,卸去钗钏,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宝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这么大福。”说着,拿了钱,便摔帘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宝玉便向镜内笑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罢,又来问人了。”晴雯笑道:“你又护着。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话。”说着,一迳出去了。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话。
这里,写麝月为宝玉篦头,引起了对晴雯的评价:“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在宝玉一生中必定是记忆犹新,于是宝玉在《芙蓉诔》化入了“愁”字,而且,在第23回的《夏夜即事》,也再有咏诵:“窗明麝月开宫镜”,但是下一句“梳化龙飞”无着落了(周先生推测诗是先做的,而故事应在23回之后的),应该和晴雯还有一段“哀折檀云之齿”的故事。既然麝月为宝玉篦头事是生活入诗,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室霭檀云品御香”,咏檀云事,也应该有故事的。但在现在留存的文本里,檀云是怡红院里很少被作者提及的一个丫鬟。至于檀云的出场,是在第24回: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秋纹、碧痕两个去催水;檀云又因他母亲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虽还有几个作粗活听唤的丫头,估着叫不着他们,都出去寻伙觅伴的玩去了。
此外,还叙述到的是第34回:袭人答应了, 送他们出去。刚要回来,只见王夫人使个婆子来,口称“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袭人见说,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告诉晴雯、麝月、檀云、秋纹等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我去了就来。”说毕,同那婆子一径出了园子,来至上房。
可见,都没有具体故事,既缺少与 “窗明麝月开宫镜”对局之“室霭檀云品御香”;也无与晴雯“梳化龙飞”嬉戏之“哀折檀云之齿”。莫非是作者后来改稿删去了故事或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们从现存的120回程本可以推测一二,将发现檀云在120回通部书里,就只有第24回里“檀云又因他母亲病了接出去了,麝月现在家中病着” 唯一提到。幸而在第23回《夏夜即事》和第78回《芙蓉诔》诗词里还保存完好。这正契合了作者早在第58回—64回王夫人等往皇陵上去时就早逝了(并没有像叙述晴雯逝世那么凄迷的结局),其故事便嘎然而止,人就蒸发了。于是,合了第77回王夫人口中 “短命死了”的谶语。
总之,从以上推理可知,第77回王夫人口中“短命死了”的“那丫头”,绝对不是柳五儿,应该就是“室霭檀云品御香”之檀云。既然柳五儿并没有早逝,那么,在后数十回中叙述“候芳魂五儿承错爱”的精彩,还是有根本的,嘲笑说柳五儿在后40回的程本中“死而复生”的荒唐,其实是有些误读了。这也并不能作为立论高续40回的一个关键矛盾的证据。
今人点评
五月之柳梦正酣(节选)
刘心武
《当代》2006年第3期
1
大观园是怎样的景象?《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对之有细致入微的描写。那些宏大的华丽空间不去说它了,在贾政和一群清客以及贾宝玉初游大观园时,有一笔过场戏性质的描写: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光这些点缀在正景之间的园林小品,就足令人心醉神迷了。
曹雪芹有意不在前面把大观园的景物写尽,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一把子四根水葱”的美人儿来荣府客居,寿怡红摆寿筵,以及第七十六回中秋品笛、黛湘联诗等后面的情节里,他很自然地补充描写了大观园里的许多景物,如秋爽斋、红香圃、芦雪广、凸碧堂、凹晶馆、翠樾埭……
“刘姥姥进大观园”,成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俗语。已故著名文学理论家,也是红学家的何其芳先生,曾提出过“典型共名说”,认为衡量一个文学形象够不够得上艺术典型,就看这一形象是否被广大读者当成了一种社会生命存在的“共名”,比如贾宝玉,人们读过《红楼梦》以后,往往就会把生活中那种自己特别愿意在少女群中玩耍,而少女们也都特别愿意跟他交往,那样的少男,称作“贾宝玉”,因此判定贾宝玉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像王熙凤、林黛玉、刘姥姥……都达到了“共名”的效果,“她可真是个凤辣子!”“你真是个林妹妹!”“我可真成刘姥姥进大观园啦!”这类人们在生活里的随口议论,都是这些文学人物因取得“共名”效应而可以判定为艺术典型的例证。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对生活中的某人指认为“真是一个王夫人!”或感叹“哪里跑来个薛姨妈!”王夫人和薛姨妈尽管也是写得颇为生动的文学人物,却还够不上是艺术典型。何其芳先生的立论在当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受到一些人批评,引起不小的争论,有兴趣的人士可以找出当年那些论辩的文章来读,不管读后是否认同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说”,但是对何先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新颖的见解,大概还都是会佩服的。任何学术课题,允许提出新说,容纳“惊世骇俗”的见解,应该是推动学术进步的一个前提,海纳百川,方呈浩瀚。
刘姥姥够得上艺术典型,“刘姥姥进大观园”也够得上是典型的人生处境。所谓“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指一个大老粗,进入了一个他或她本没有机会进入的高档空间,意味着侥幸,也往往表示着“猪八戒吃人参果,那么好的东西却品不出味儿来”的意思。顺带说一下,以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说”来衡量《西游记》里的角色,那么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白骨精都能成为“共名”因而够得上是艺术典型,沙和尚难以成为“共名”,因而就够不上。
刘姥姥不仅是侥幸,简直是幸运,贾母把她带进入大观园让她逛了个够,问她:“这园子好不好?”她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刘姥姥比猪八戒强一些,对大观园这个“人参果”还算有点“比年画还强”的审美感受,但从粗陋空间闯进精致空间,她出恭后一个人迷路绕到了怡红院,虽然对呈现于眼前的各种事物不断吃惊,却全然没有审美愉悦产生,最后竟仰身倒在宝玉卧榻,一顿臭屁,酣然一觉。一个生命的惯常空间,养成了一个生命的惯常思维、惯常情感和惯常的行为方式,那是很难改变的,除非他或她还年轻,对于从现有的粗陋的生存空间挣脱出去,进入一个精致的高层次空间,并且能在其中长久立足,还抱有热切的憧憬与付诸行动的勇气。
曹雪芹写大观园,最厉害的一笔,我以为是在第六十回,大观园什么模样?“也没什么意思,不过见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大观园宜作面面观,在有的人眼里,所看到的景色,竟不过尔尔。
那是谁眼里的大观园?
2
那样形容大观园的,是柳五儿。
柳五儿是内厨房管事柳嫂子的女儿。
大观园建成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单设厨房,住在园子里的宝玉、李纨和众姐妹们,到吃饭的时候还得走出大观园,到上房,也就是王夫人那里,或者贾母那里去吃饭,这在书里是有描写的。大观园里的丫头们又到哪里吃饭呢?书里没有明确交代,估计更是要走出园子,去跟园子外的那些丫头们一起吃饭。大观园本身不小,出了大观园到王夫人或贾母那边,还要走很多路,到了秋冬和春寒时分,园子里的人吃饭真是很不方便。于是,作为荣国府实际上的总管,王熙凤有一次就提出来,在大观园后身单设一个厨房,也就是区别于府里总厨房的内厨房,专门供应住在园子里的主子和丫头们的饭食。这是在第五十一回末尾交代的。王夫人首先赞同:“这也是好主意。刮风下雪倒便宜,吃些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风,压上些东西也不好。不如后园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他们姊妹们弄饭,新鲜菜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房里支去,或要钱,或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一个厨房多事些。”王熙凤就更坚定地表态:“并不多事。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冷风朔气的,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何况众位姑娘。”于是拍板定夺,大观园内厨房开张。
主子们一项新政的推行,会给下面仆役层里的一部分人带来实际利益。
“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从后面的描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被挑为内厨房总管的只是一个女人,就是柳嫂子。
柳嫂子原来在梨香院里管点事,可能就是那里的厨子。梨香院原是荣国公用来打坐静养的一个空间,一度闲置,薛姨妈一家从南方进京投奔荣国府后,在里面住过,后来又从那里搬到另一处院落,为筹备元妃省亲,贾府派贾蔷从南方买来十二个女孩子,训练她们唱戏,每个女孩都认一个妇人为干妈,十二个女孩也就是“红楼十二官”,在梨香院集中居住排练时,女孩们和那里的妇人们关系就很复杂,有处得好的,有处得不好的,而其中唱小旦的芳官,和柳嫂子关系非常之好;再后来,由于朝廷里薨了老太妃,元妃不再省亲,贵族家庭不许演戏,贾府就解散了梨香院的戏班子,十二官里死掉了一个,有三个不愿意留在贾府另谋生路去了,还有八个则被分配给贾府的主子当丫头,芳官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了怡红院,并且很快得到宝玉宠爱;八个留下的唱戏姑娘的干妈,随干女儿到各房中为仆,而芳官的干妈的亲女儿春燕和小鸠儿,也正是怡红院的丫头,人际关系,交错纠结,写得很有意思。
芳官的干妈何婆,开始对芳官很不好,掌握着芳官的那份月钱,却不往芳官身上使,芳官洗头都洗不痛快,于是爆发了怡红院里有名的“洗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芳官的干妈对芳官很苛啬,但是,柳嫂却对芳官非常好,投桃报李,芳官因此也对柳嫂格外关照。
曹雪芹写大观园,写大观园里的生命,是立体的写法,他不仅写主子,写丫头,也写相对底层的仆役小厮,写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诉求。第六十一回开头,他特意写了一段剃杩子盖头——杩子就是马桶——的小厮,跟柳嫂子在后角门发生口角的情节,这些“过场戏”绝非可有可无的文字,而是使《红楼梦》的文本更丰满更精致,更能揭示世道人心的精彩笔触,建议大家读时不要草草掠过。
那杩子盖发型的小厮,扭着柳嫂子,求她从园子里摘些果子来给他吃,柳嫂子就说他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意思是那小厮的舅母姨娘就是园子里承包管理果树的,不问她们去要,却要到自己跟前来,小厮听了,就反唇相讥,揭出柳家的一桩隐私来,那就是柳家的女儿“有了好地方了”,柳家的不承认,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就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柳家的女儿柳五儿,正谋求到“好地方”去“成个体统”,此事正进行中,尚未实现,但是,就连看角门的芥豆小厮,也都知悉。柳家的内牵,就是芳官,芳官已经跟宝玉推荐了柳五儿,因为林红玉口角伶俐办事爽快被王熙凤要走,怡红院的丫头编制恰有空缺,柳五儿的补进,正逢机会。本来这事也不复杂,但是,柳五儿自己有个弱症,需调养好才行,而大观园里又正逢“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乱哄哄的情况下,贾宝玉也顾不上点名要人。于是,虽然前景美妙,柳五儿一时却还只能窝在大观园之外,灰色生存。当然,因为她母亲是大观园内厨房的管事,她能够进入角门,在大观园后身作为厨房的那五间大房子内外活动,那也算是大观园的一部分了,再往里,她是不敢随便去的,但又常常忍不住把脚步往里迈,把身子往里移,一颗心怦怦然,想偷窥一下园中美景,但那山子野设计的园林,把主子活动区与厨子杂役类奴才劳作区,分割得非常清晰,用许多的大山石大树木和高墙屋壁,形成一道屏障,将二者互相遮蔽,于是咫尺天涯,人间两域,柳五儿在“不成体统”的时候,是不能越雷池而触戒律的。
可怜的柳五儿,她胆气壮时,也曾试图多往里走走,但所看到的,当芳官问起来时,也只能感叹:“今儿精神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不过见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
一个生命,向往着一个自己暂时去不了的空间,这是人世间最常见的心态。
3
生命和空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也需要探讨,但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似乎不那么迫切。“我为什么没生在唐朝而生在了现在?”有这种追问的人实在很少。“我为什么没赶上抗日战争?要那时候出生参加打鬼子的战斗多来劲儿!”这类话语虽然会偶尔听到,但完全用不着认真回应,不过说说而已。绝大多数人都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出生时间,珍视自己的生日,即使对于所处的时代有诸多不满,但深知自己的生命不可能更易到另外的时段,因此,对于自己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也就往往不再去深想细究。
但是,在同一时间段里,生命和空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个转移的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以前,拿北京来说,同在一城,都是少年,“大院里的”和“杂院里的”,两种生活空间,生活状态、心理定势、语言特点、情感表达……就会很不一样。那“机关(或部队)大院”的空间,与“杂院”的空间,可能就在同一条胡同里,甚至相互间只有一墙之隔,但墙两边,两种空间里,人生状态却会有明显的不同。还有一种高级四合院的空间,也就是首长住宅,那个空间里的生活状态,跟“大院”里的又有所不同。在那个历史阶段里,一个“杂院”空间里的少男或少女,就往往会羡慕“大院”空间里的“革干”(或“革军”)子弟,有的就可能会像《红楼梦》里的柳五儿一样,憧憬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转移到那样的一个,比自己所出身的空间更高级的空间里,去品尝人生的更甜蜜的滋味。
改革、开放以后,生命对空间选择的自由度,被空前展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拥进城市,城市的青年人出国留学,近十几年来,更有许多国人拥到世界各地经商,有的人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借高利贷,筹重金交给蛇头,去偷渡到自己心目中的“大观园”,结果酿成悲剧甚至惨剧。
“进入大观园啊!去到怡红院啊!”柳五儿那样的追求,直到今天,仍是许多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目标。
2000年春天,我和妻子吕晓歌应法国方面邀请,在巴黎访问。英国的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顺便发出邀请,请我携夫人往伦敦讲两场《红楼梦》,一场在伦敦大学给东亚系汉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一场则面向普通伦敦市民。我接受了邀请,但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申根协议,我和妻子虽然有法国给的签证,持那签证虽然可以免签前往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许多参加了申根协议的国家,却不能前往英国,去英国还需到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领事处再办签证。
我和妻子去了英国在巴黎办理赴英签证的地方,那里的签证官见我们是中国人,眼光似乎有些异样,他找来一位负责的女士,那女士板着个脸,说我们不应该到她这里来申请签证,我们应该在北京申请;她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跟她解释,已经跟他们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电话,参赞说因为邀请我们的机构是英中文化协会,此协会的背景就是英国外交部,所以可以破例;那位女负责人当即与他们的主管部门通了电话,得到证实,于是决定给我们签证,就在这时,她跟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法国朋友把大意翻译给我听,我一听就急了,就说我不去了,别给我签证了,把我的中国护照还给我!
我为什么生了大气?原来,那位负责发放签证的女士嘀咕的是: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当然,刘先生跟那些多佛的中国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不特别谨慎啊!
原来,就在我们去办签证的前一天,正好发生了一件轰动英国的大事:一批中国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从法国渡海到了英国多佛口岸;本来,那集装箱上有个通气口,可是开车的司机怕检查时漏馅,渡海时给堵上了;但英国口岸的海关抽查,偏查到那辆车,打开集装箱,挪开货物,立即发现了若干已经窒息毙命的中国偷渡客。英国报纸在报导这件事情时,特别强调,有几个负责检查的海关工作人员,因为突然目睹了扭曲的死尸,不仅生理上立即发生呕吐晕眩等症状,而且也很快派生出心理问题,已经立即有心理医生在对他们进行治疗云云。
那些离乡背景的中国偷渡客,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同胞!他们违法,他们糊涂,他们冤枉,他们不幸,但是,他们毕竟是想通过转移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谋求更幸福的生活啊!
我跟他们,一样的黄皮肤,一样的黑头发,血管里,流淌着同一祖宗传下来的血液,“你们中国人,总想到西方”,尽管那位英国外交官试图把我和我妻子跟我的这些惨死的同胞区别一下,但乍见到我们时,那冰冷的眼光,那板起的面孔,不也分明表达着一种对中国人的“特别谨慎”,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吗?
人家那个签证厅,是不许大声喧哗的,可是在那一刹那,百感交集的我,大声嚷了起来:“还我护照!我不去了!”
法国朋友制止了我,妻子也低声批评我,英国外交官莫名惊诧,但最终还是给了我们签证。我和妻子是在复杂的心情中乘海底隧道火车,从巴黎前往伦敦的。
从那以后到现在,六年过去,在报纸上,仍有中国人以偷渡手段前往国外,被查获遣返,或侥幸抵达,而惨遭变相囚禁、剥削虐待的新闻。
而在这篇文章刊发以后,相信也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只是,或许会逐步减少些吧。
为什么总有一些中国人,孳孳汲汲地谋求生存空间的大转移?如果所有的这类转移都只是悲剧,那就无法解释其心理依据。我们必须承认另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有数量很不少的转移者,在那边空间里立了足,融进了那个空间,有了物质和精神上都很不错的生活,请他们的父母去探视、旅游,也偶尔会来探亲访友,令亲人欣慰乃至引为骄傲,被邻里旧识羡慕甚或嫉妒;还有一些转移者,其中不乏开头以非法手段转移,又非法滞留不归,但终究还是从非法转换为合法,又以合法身份发了财,衣锦还乡,光耀乡里,成为来当地投资的“外商”,被当地政府官员高规格接待,甚至被安排为政协委员,那样的更具传奇性、喜剧性的人物存在。
我在伦敦的演讲,没有提到柳五儿,但也就在那期间,我就存下一个念头,探究一番柳五儿的“移民美梦”。
6
我也曾一度觉得,柳五儿那样向往去当稳一个女奴,实在是空间认知与抉择上的一个失误。
顺着那样的感觉,可以很顺溜地推导出来一串逻辑:柳五儿的正确抉择,应该是去寻觅农民起义的空间,投奔其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样的空间里燃放出夺目的光彩。
把目光投向现实,似乎就应该谴责那些力图将生存空间移往境外,或在国内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同胞。
但是,冷静下来,我就觉得,《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生存空间,真实可信,其中每个生命的空间追求与存在状态,都包含着一定的天理。
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制。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
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异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
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还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2000年“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静夜里,因《红楼梦》的柳五儿,竟浮想联翩到这样的程度。感谢曹雪芹,你的文字,启迪、滋润着我的心灵。
2006年3月8日绿叶居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