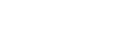史嵩之(1189年-1257年10月6日) ,字子由,一作子申,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名臣,尚书右仆射史浩之从孙、右丞相史弥远之从子、提举福建盐茶事史弥忠之子。
史嵩之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中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后任襄阳户曹。历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要职,经营襄阳,抵御蒙古入侵。嘉熙四年(1240年),入朝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为相期间以专断而受非议。淳祐四年(1244年),史嵩之遭遇父丧,希求夺情起复,因主张和议,遭到舆论反对。闲居十三年,不再出仕。宝祐五年(1257年),史嵩之去世,年六十九。获赠少师、安德节度使,追封鲁国公,谥号“庄肃”。德祐初年夺谥。著有《野乐编》,已佚。《全宋诗》录有其诗。
后世对史嵩之褒贬不一,认为他颇有才能、功勋显赫,但同时又追求权力、专横独断。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史嵩之出身显赫,他的从祖父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孝宗在位时一度官拜右丞相;从叔史弥远在开禧北伐时通过弑杀外戚韩侂胄而成为宋宁宗、理宗时期的权臣;父亲史弥忠,官至提举福建盐茶事,为政有能,且不攀附史弥远,在诸子显贵后,仍朴素如初。
史嵩之年少时风流倜傥,曾在东钱湖梨花山读书,他所接受的是陆学与吕学中的事功学。史嵩之行事果断,似乎更喜欢事功之学,而不喜欢朱学人士的迂缓。一次他与内弟陈埙讲学在山寺,山寺的僧人讨厌他,史嵩之很恼怒,当夜就焚烧其庐而去。
嘉定十三年(1220年),史嵩之中进士,调任光化军司户参军。不久,史弥远问史嵩之说:“给你换一个新的职位,你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希望能到襄(阳)汉(水)一带去做官。”史弥远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了。即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然而史弥远虽然在相位日很久了,却其实并不知襄汉的表里。史嵩之似乎对荆襄地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时,他便能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
经营襄阳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淳熙年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
史嵩之也同时具有这种眼光,从自入仕以后,他几乎一直都呆在襄阳一带:
嘉定十六年(1223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
嘉定十七年(1224年),升任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干办公事;
宝庆三年(1227年),任京西、湖北路制置司主管机宜文字,回襄阳府任通判。
绍定元年(1228年),史嵩之在襄阳经理屯田,积谷达六十八万石。被加官,并奉命权知枣阳军。次年,调任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不久后兼任制置司参议官。
绍定三年(1230年),枣阳军的屯田工作再获成功,史嵩之也因此升官二级。后又因祭祀明堂赐恩,又被封为鄞县男,加赐食邑。随后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又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
绍定四年(1231年),自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次年升为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旋即升授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至绍定六年(1233年)加迁刑部侍郎。自此,史嵩之正式成为了京湖战区的帅臣。
史称他常常暗中将襄阳地理和撤戍增防的机要情况报告给史弥远,于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便成为了京湖帅臣。他努力经营襄阳,开展屯田,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为坚固襄阳的防守备足了粮草和兵马。
联蒙灭金
绍定六年(1233年),大蒙古国的窝阔台汗遣使臣王楫南下来到京湖,与史嵩之商议协同进攻金国、支援蒙军粮草的事务,并许下诺言,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归宋廷所有。史嵩之便奏报朝廷,请予批准。
十月,宋廷在史弥远的决策下,决定联蒙灭金,命令京湖制置司出兵。史嵩之于是派江海、江万载叔侄携孟珙等领兵两万、运粮三十万石,奔赴蔡州。至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孟珙携带金哀宗一半的尸体及金国皇帝的仪仗器械和玉玺等宝物凯旋而归,金国彻底灭亡。这其中自然有史嵩之善于用将士的功劳。因此这一战给史嵩之带来了无限的声誉,同时也使理宗看到了他的才能。
端平入洛
金亡之后,理宗虽然献俘太庙,但蒙古却不归还河南地区。根据当时形势判断,宋、蒙早晚必有一战,守将赵葵等因此提出了据关守河的策略,并得到了丞相郑清之的支持。但这一战略实在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于是就拿到朝堂来进行讨论,这时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其盟友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乔行简主和是一贯的,但其实这次反对“据关阻河”,更多的出于乔行简个人的因素,他早有结盟取代郑清之的企图。由于理宗亲自决策,朝廷最终商议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非策;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一口回绝。
尽管史嵩之反对出兵,但理宗与郑清之还是让他负责筹画粮饷,史嵩之以“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为由推辞,并再次表达了自己反对入洛的立场。既然朝廷已经决策,郑清之以为必须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于是就写信给史嵩之,叫他“勿为异同”。史嵩之还是力求辞去此职,但最终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事实上,自史弥远去世后,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成了结盟,并帮助乔行简谋相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他不愿同郑清之合作。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全子才帅前部进入开封,接著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也赶到汴京,并且不顾粮饷未集的情况,将远道而来的队伍强行编成两队,分别由徐敏子、杨义指挥,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的第二天,之前携带的五日军粮已在过去的八天里吃完,宋军开始“采篙和面作饼而食之”。而当天夜里,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一万五千余人行军至龙门,遭到蒙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随后的龙门一战,徐敏子所部一触即溃,被蒙古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十之八九。因史嵩之及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屡次不理朝廷促粮的诏令,粮饷不足,入洛宋军只好弃洛退归。于是,端平入洛以宋军损失近三万,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
事后,理宗下诏追究责任,称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郑)清之,准令免职。”
入朝拜相
端平二年(1235年),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军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以乔行简为相。这时的理宗一心想达成和议,派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去前线督战,史嵩之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并力主和议。遭到大臣李宗勉的批评,他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起居舍人袁甫说:“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瞭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说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监察御史王遂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刚回来,就遇到蒙古派将军忒木觫进攻江陵,史嵩之在黄州,即遣人给孟珙下达增援江陵的命令。孟珙驰赴江陵,连破了蒙古军二十四阵,夺还了被俘的二万人口,江陵之围就这样解住了。史嵩之因功于嘉熙元年(1237年)进官华文阁学士。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东路军的一支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而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府,各地守臣弃城而逃。史嵩之檄令孟珙从江陵前来增援,将口温不花击退。孟珙智勇善战,连胜两仗,使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一时朝野振奋。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他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宋廷就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令他恢复郢州、荆门,以便巩固江陵的北面屏障。
嘉熙三年(1239年),孟珙出兵,连续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史嵩之则被理宗擢为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开府鄂州,成为宋廷前线的最高统帅。虽然孟珙接连获胜,但史嵩之仍主和议。这年九月,蒙军又以和议未能达成,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动用了号称八十万的大军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淮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作为最高统帅的史嵩之又一次得到了理宗的奖誉。
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史嵩之竭力附和。右司谏曹豳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但理宗与史嵩之观点一致,就派遣通好使,去与蒙军谈和。
自郑清之罢相后,史嵩之就有意于相位。他企望史氏能重新得到宠爱,更企望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
嘉熙四年(1240年)三月,史嵩之被理宗召回临安,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进封奉化郡公,实现了他多年振兴史氏的愿望。
史嵩之大权在握,为了筹画前哨江防,他迫令征集渔舟。大臣康植反对说:“令征渔舟,渔民无以为生,万万不可。”史嵩之劾奏将他贬为江陵酒官。
嘉熙行政,最终形成了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格局。当是人们的评价是:“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
淳祐元年(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史嵩之进《玉斧箴》,又挤掉了乔行简,独自柄国。
此时,越南陈朝向南宋进贡,却不用南宋正朔,史嵩之建议用宋仁宗时范仲淹退西夏国书的例子,以“不敢闻于朝”的理由拒绝此次入贡。
大臣高斯得上奏,请求择才与史嵩之并相,史嵩之很恼怒,就指使他的党羽说高斯得叔父兄子不可以同在朝,将其外放通判绍兴。
淳祐二年(1241年),《四朝帝纪》一书写成,史嵩之不顾反对,改掉高斯得所草的《甯宗卷》中对于济王的评论,然后进献,同时又进献了《孝宗经武要略》《甯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等,被进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增加食邑。同年冬,进封永国公,再加食邑。
史嵩之行事果决,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的事业构成阻力,就会加以除去。
淮西制置使杜杲上奏表示和谈只是蒙古诡计,曾令史嵩之十分难堪,因此他指使台谏弹劾杜杲,夺去其兵权。
史嵩之入相时,曾召师雍(史弥远弟子,但不与史弥远合作)审察,并秘密示意主动与他改善关系,然而师雍不领情;史嵩之迁师雍到粮料院任职,并说:“粮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还是不领情。嵩之独相后,博士刘应起首先上奏论史嵩之的过失,理宗被说动了,想驱逐史嵩之。因为师雍与刘应起友好,所以史嵩之怀疑是师雍在中间作梗,就指使御史梅杞攻击师雍,朝廷就差师雍知兴化军,不久又改知邵武军。
道士孙守荣曾遇到异人,异人授他一支铁笛,他常常吹着笛在市中行走。后修道有成,能预测遥视。一次他去拜谒史嵩之,门卫谎称史嵩之午休,不让他进去。孙守荣当即指出史嵩之正在园池钓鱼,怎么说是在午休。门卫非常吃惊,便入报史嵩之,史嵩之颇喜欢孙守荣的言谈举止和仙道风雅;孙守荣则坦陈己见,发生在史嵩之身上的许多事都被他一一说中了,史嵩之不舒服,终于将他贬死在远郡。
史嵩之为政专断,因而招来广泛的不满,虞复上表《爱养根本之说》,极力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也被降职任都郎官。李昴英就写了一篇《论史丞相疏》上奏,揭露史嵩之。
父忧离职
淳祐四年(1243年)九月,史嵩之的父亲病故,但他却贪恋权位,不肯守孝,竟援引战时特例,企图自我起复。结果自然引来了一片反对声,四明当时流传著这样十七字说:“(马)光祖做总领,许堪为守臣,丞相(指史嵩之)要复起援例。”临安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人都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他们对史嵩之的“专”愤愤不平,发展到此次事件,遂一发不可收拾。
而理宗努力起用史嵩之,既有感激史弥远的原因,也有看重史嵩之才能的因素。理宗与徐元杰有一段私下对白:上问:“史嵩之起复如何?”奏云:“陛下以为如何?”上曰:“从权尔。”奏云:“此命出於陛下之心乎?出於大臣之心乎?”上曰:“出於朕意,朕以国家多事,用祖宗典故起之。三学生上书,卿曾见否?”奏云:“闻有此书,尚未之见。”上曰:“人言太甚。”上曰:“朕自当优容之,但边事亦罕有熟者,史嵩之久在边间,是以起复。”这段对白说明了一切,理宗需要史嵩之,边间需要史嵩之。
但由于史嵩之当国时,深深地得罪了公论。而史氏已有史弥远一个在位二十六年,人们不愿意再让史氏长期任相了。故而朝中反对他的大臣借此起复发起的一场攻讦运动,其规模之大、语言之激烈都是宋代历史上罕见的。最终连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都写信对他大加指责。
史嵩之为相期间,与他共政的先后有十名执政,但他们大都无权力,即使是始终与史嵩之共政范钟也如此。
总论的史嵩之的相业,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史嵩之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贤相”。这一点还可从别人对他的攻击中反映出来:今(淳祐初)任用混肴,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其(史嵩之)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可见在史嵩之领导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这显然有利于克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嵩之执政时,废十六界,行十七界,以二准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仅值铜钱五十文,十八界值二百五十文。从嘉熙四年至景定五年,二十五年中,百姓颇为安顿。他还采用专卖政策,增收财富,拨赴边州。他任职期间边防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特别是余玠在四川实行的山城防御计画以及孟珙对襄樊的建设,这些都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很多人都不这么看,《宋史》论曰: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显示人们是因否定史弥远而完全否定史嵩之,而这种否定是先验的。在大臣们的反对下,理宗最终放弃了复用史嵩之的打算。
失意而终
同知枢密院事杜范得到乔行简的提拔,位列执政,与中书舍人徐元杰、户部侍郎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他不屑与史嵩之共事,辞职回乡。理宗让人追回,并命令临安各城门的官员不得让杜范出城。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挽留杜范,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史嵩之。史嵩之久擅国柄,为了平息舆论,他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于是六次请求辞相,理宗果然不批准。但杜范一派的大臣却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驱遂史嵩之。刘汉弼就秘密上奏理宗说:“现在史嵩之既然多次请求辞职,就让他去为父守丧吧。皇上应当选择贤臣,早日笃定相位。”理宗狠下心来,采纳了刘汉弼的建议,同意史嵩之请辞。但不过几日,又回心转意,准备重新起用史嵩之。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朝廷哗然失色。徐元杰认为理宗这种做法是游戏国事、出尔反尔,於是“攻之甚力。”这时太学生们又纷纷上书坚决反对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放弃起复史嵩之的打算。
淳祐四年(1243年),范钟进拜左丞相,杜范入拜右丞相。当时范钟身为首相,但实受制于杜范。
杜范拜相后,发布了一系列措施,临安士民欢呼载道。杜范又擢徐元杰为工部侍郎,一切政事都与他商议。谁料不久后,杜范竟暴病而亡,在相位不过八十日。还没有过一个月,徐元杰也暴毙身亡。三学诸生听说此事,都说徐元杰是被人谋害而死的,他为抱不平,於是伏阙上书,说“历期以来,小人之倾陷君子,不过使之远谪,触冒烟瘴而死。今蛮烟瘴雨,不在岭南,转在朝廷,臣等实不胜惊骇!”理宗见了此书,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但没有进展。随后,刘汉弼又忽然得病身死。
三人相继暴死后,太学生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三人叩阍上书,为之讼冤。众议愈加沸腾,竟有人说杜范中毒而亡,在廷诸臣无不人人危惧。就在这时,史璟卿也暴病而亡。有了这件事,大家都怀疑到了史嵩之的头上。
有的议论还说得有根有据:一年,史弥远的儿子史宇之休了他的媳妇洪氏。据说是因为对林氏不够孝顺,林氏是史弥远的嬖妾,因深得宠爱,平日淫纵自如,她为弥远只生一子,即宇之,宇之娶洪氏,而洪氏不能与林氏合污同秽,妨碍了林氏淫纵,林氏就叫宇之休出洪氏。杜范得知就上奏说:“朝廷应当戒谕史氏,弗使丑声有闻。”理宗没有过问。不久林氏死了,理宗给予恩泽,恤典极盛。杜范又上奏说:“皇上因为林氏是卫王(弥远)嬖妾而曲徇其情,为什么只是不想一想洪氏是卫王的媳妇呢?”当时嵩之在相位,因此杜范上奏中就有:“宰臣(嵩之)本来是卫王的同族,连这样的家事都不管,那他还能凭什么来治理天下呢?”杜范也的确管得太宽了,史嵩之听到后,非常气愤,自然把对杜范的恨心都记在心里,何况杜范在理宗心目中地位日高,必谋相位,于是史嵩之就差人去摸透杜范的习惯。史嵩之去相,而取代他的就是杜范,史嵩之再也不能容忍,他得知杜范平素嗜书如命,便用毒药涂在书简上,叫人献给杜范,杜范旦夕翻阅此书,毒气蒸目,就失明死亡。这些都只是一种猜测,但当时史嵩之为公论所不容,却是事实。
理宗于是御笔除授史嵩之祠官。史嵩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回乡。在住地建设府第,并在附近建云树壁、钓鱼台、三溪桥,闲居在此。期间,理宗曾三次想恢复史嵩之的职务,一次是淳祐六年服丧期满,一次是淳祐十年,郑清之将不久于人世,另一次是宝祐四年,史嵩之表示晚岁愿守蜀,但每次都因遭遇强烈的反对而无果,致使史嵩之闲废十三年,终不得复出。
宝祐四年(1256年)春,史嵩之被授为观文殿大学士,加封食邑。
宝祐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257年10月6日),史嵩之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朝廷追赠他为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进封鲁国公,谥号“忠简”,因为家讳改谥“庄肃”。德祐(1275年-1276年)初年,因右正言徐直方进言,史嵩之被夺谥。
主要影响
史嵩之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任相以后,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二人在抗御蒙古南侵的战事中都功绩卓著。
历史评价
脱脱: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
王夫之:①夺情之言扬于廷,人子之心丧于室矣。蝇蚋不嘬生而嘬死,有以召之也,而况纷呶自辩以与公论相仇!史嵩之、李贤、张居正、杨嗣昌之恶,滔天而无可逭矣。②至于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③(会蒙古以灭女直)君国者,理宗也;秉成者,史嵩之也;继之者,贾似道也。④尸大臣之位,徼起复之命,以招言者之攻击,自史嵩之始,而李贤、张居正、杨嗣昌仍之。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
主要作品
史嵩之诗文颇佳,《甬上宋元诗略》载其《雪后》诗云:“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稽如下雨,祐涧忽鸣湍。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写雪融之景,视野开阔,描摹细微。
史嵩之著有《野乐编》,已佚。《全宋诗》卷3161录其诗三首。《全宋文》卷7684收有其文。
人物争议
在史嵩之墓发掘前,史料多有误认为史嵩之是史浩之孙的记载,而据墓圹志显示,史嵩之为史诏四世孙;史嵩之的祖父为史渐,是史浩的堂表兄弟;史嵩之的父亲为史弥忠,史弥忠与史弥远是堂表亲的关系。
而圹志还记载着史嵩之卒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与《宋史·理宗纪》相同,足以证明《宋史·史嵩之传》宝祐四年之说的错误。
后世纪念
诗词
吊史相
元·戴帅初
日晏霜浓十二月,林疏石瘦第三溪。
云沙有径萦寒烧,松屋无人鸣昼鸡。
几聚衣冠块作土,当年歌舞醉如泥。
早知涉世真成梦,不弃山前春雨犁。
史嵩之
三溪桥吊史相
明·柴孝东
雨洗东山一振衣,过桥草树正霏霏。
茅庵小坐成清绝,竹径双开对翠微。
石壁尚存云栈迹,溪浪故绕钓鱼矶。
可怜丞相家何在?水自涓涓鸟自飞。
墓园
史嵩之墓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车厩五联村林夹岙山腰,于2011年12月,由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史嵩之夫妇墓由北向南全景
史嵩之墓南高北低,呈西南东北走向,由墓园和功德坟寺组成,目前墓园已经面目全非,寺庙遗址保留。2011年发掘墓园内的墓室部分,共清理古墓葬4座,其中两座为清代晚期平民墓葬;另两座分别为南宋右丞相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之墓。
史嵩之夫妇墓均为长方形石顶砖椁单室墓,南北平行相距两米。古墓由“甬道、排水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顶顶端覆盖着一整块经过雕凿的梅园石大石板,石板长3.8米、宽1.9米,厚40公分,重量超过8吨。“之所以确认这是史嵩之墓,是在墓顶石板中央覆盖着一块长方形圹志,上面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及其家族情况,明确了这是史嵩之夫妇墓。”圹志中除记载了史嵩之夫妇埋葬的具体位置,还记载了史嵩之的生平、官职及子孙等家族情况。圹志中最有价值的是为研究史氏家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弥补了史书不足及错误之处。
史嵩之墓出土玉佩
史嵩之墓被盗严重,出土器物不多。其中的一具赭红色漆木棺,木棺主体保存较好,长2.37米,宽0.7米,高0.92米,木棺厚10-11厘米。在木棺破损前盗洞处,发现了一件玉佩,一件镏金铜环、水银若干、少量古铜钱及丝织品残骸。这件“和合二仙”玉佩雕刻精美,镏金铜环由方形和圆形相连,鲜亮如新,环上还残留着灰黄色的纺织物。
墓中出土的保存尚好的丝织品为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填补了浙江省乃至中国南宋服装史研究的空白,对于南宋浙东经济史、手工业和纺织业技术史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
此外,赵氏墓葬同样曾经被多次盗扰,除出土少量古钱币和1枚金钗外,墓室空无余物。考古专家分析:“赵氏圹志为史嵩之家族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宋代赵氏宗室及明州(庆元)史氏望族、宋代宁波地方史志也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据记载,赵氏为史嵩之继室,生三男六女,死后被封为“魏国夫人”。
史料索引
《宋史·卷四百一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