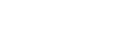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法哲学3个
作者简介:约翰▪杜威(John Dewey),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文章来源:初译稿原刊于《法理学论丛》第6卷,此为修订本。译自My Philosophy of Law: Credos of Sixteen American Scholars, Boston Law Book, 1941, pp. 73-85.转引自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论坛公众号。
译者为姚远(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透过各流派学说及其间的争论,来考察法律的性质问题,便发现该问题至少分为三个相互有别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三个议题涉及法律渊源(source)、法律目的和法律适用,法律适用又包括有关我们实际和能够使法律产生效用的方法问题。
所谓哲学性的法律探讨所牵涉的各种问题,似乎源于这样一种需要,即拥有某些原则,以便证成(justify)和(或)批判现行法律规则和法律实践。这一需要和动机或许在如下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彰显,那些哲学在它们所谓的实定法(positive law)和自然法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并且自然法被用作实定法应当实现之目的,以及应予符合之标准。当下,这种特殊的程式化表述只是特定思想流派的风尚,该流派依旧恪守那在中世纪得到表述,并持续影响到整个17世纪欧陆法学家的总体思路。然而,如下区分和需要似是法哲学领域全部运动的背后支撑力量(be back of):(1)区分某一时间碰巧存在的事物以及可能和应然的事物;(2)需要某种有关可能和应然事物的观念,它将为组织、证成和(或)否定、改革现存事物的某些方面提供“原则”。
照此看来,对法律渊源和法律目的之探讨可以合并为一个主题,即据以评价现行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的标准或准绳。“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于是化约为“人们相信那些规定和实践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根据那些极富影响力的传统,目的和标准的确定,与终极渊源的确定密切相关——当上帝“意志”或上帝“理性”、或者终极且固有的(ultimate and intrinsic)“自然法”被奉为法律渊源时,情况显然如此。把渊源等同于目的和标准,这种做法背后藏有一种信念,即除非能够找到比经验更高级更固定的渊源,否则对实存法律的任何真正哲学评价便没有确凿的根据。因此,诉诸渊源不同于诉诸时间中的起源(origin in time),因为后一种程序把问题与经验挂钩,也就与古典传统(classic tradition)加在经验性(experiential)事物上的一切缺陷挂钩。
前面的引论有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旨在表达如下信念:所谓“法哲学”的探讨包含一个真正且重要的问题,即能够根据什么来正当且有益地(legitimately and profitably)评价现行法律事务,包括法律规则、立法工作、司法判决和行政实践。另一方面旨在表达:事实上,各种法哲学素来反映着(且势必继续反映)其诞生时期的各种运动,因而无法与这些运动所表征的东西分离开来。
最后这句论断比较宽泛。对许多人而言,它似乎回避了(beg)法哲学所关注的一切重要问题。然而,就过去的各种体系而言,它意味着在看待那些体系时,须同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该观点还认为,当那些哲学被视为种种实践尝试的体现时,它们的实际意义得以强化。因为如果基于单纯知性立场看问题,五花八门的法哲学彼此针锋相对,不啻意味着它们全都在尝试无稽之谈。若依本文提议的观点,则它们拥有其反映的那些运动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它们的冲突不断证明某种生机盎然的真实性。同理,假如本书收录的不同文章代表着各不相容的立场,那是因为它们表达了对“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得最好”这两个实践问题的不同态度。无论如何,我本人要谈的东西正是以这种精神提出的。从根本上讲,我给出的是要在行动中加以检验的行动计划,而非某种可基于纯粹知性进行判断的东西(事实断言和逻辑一致性问题除外)。
我所采取的立场是:法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社会现象(law is through and through a social phenomenon);在起源上、在目标或目的上、在适用上,法律都是社会性的。我们在说出或写下“社会性的”(social)这个词时,不会注意不到伴随着社会和社会性的这两个词的各种歧义和论争。此处,可能有人以如下理由反对前述观点:前述观点试图通过参照更加模糊的东西(即社会),来解释本就模糊的东西(即法律的性质)。但就本文宗旨而言,有必要对“社会性的”一词的含义仅作两点陈述。我假定,无论该词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它首先指向人的活动(human activities),其次指向这些活动所表现的行为方式,即交互活动(inter-activities)。说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是活动,从否定的方面,意味着它们不是如下类型的“事实”,即已然做到、完成和结束的东西;从肯定的方面,意味着它们是过程,是持续发展中的东西。甚至当我们面对既往的事件时,如果所考虑的是社会事实,那么就得承认:那些事件代表着一系列时间片段,它们有足够长的维度来覆盖各种初始条件,以及后果或结局的后续阶段,后者转又成为一种持续发展中的东西。就法律而言,该立场意味着我们须以如下方式看事情:法律与其他活动错落交织在一起,同时法律本身又是一种社会过程,而非可以说在某一日做成或发生的东西。这前半句的意思是,我们不可将“法律”确立为仿佛自立门户的实体,而务必在探讨法律时,联系其诞生时的社会状况及其具体施为。正是有鉴于此,把“法律”一词作为单独全称词项(a single general term)来用才颇为危险,我需要明确指出,“法律”一词乃是总结词项(a summary term),用它是为了省去重复提及法律规则、立法和行政活动(在后者对人类活动过程施加影响的范围内)、司法判决等等的麻烦。
那后半句[译者注:指“法律本身又是一种社会过程,而非可以说在某一日做成或发生的东西”。]含有如下结论:所谓[法律]适用,并不是在规则、法律或制定法确立之后发生的东西,而是它们的必要部分;这部分确系必要,因为在给定案件中,我们要判定法律事实上是什么,就必须澄清法律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法律对持续发展中的人类活动造成什么影响。“可适用性”(applicability)一词的含义,可因特定目的而受到更多技术性的限定。但从可称得上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须对“适用”作出宽泛的理解。某一给定的法律安排就是该法律安排所为之事,而它所为之事无外乎调整和(或)维持作为持续事务的人类活动。倘若不加适用,则存在的只是悬而未决的纸片或声音,根本谈不上法律。
或许,当我们说社会活动就是交互活动时,所传达的意思仿佛已被“社会性的”一词所涵盖,因为该词意味着联合(association)。然而,我们提请读者特别留意这个特点,是想说社会行为的一切事实中,都存在事实上的(de facto)——尽管未必是法律上的(de jure)或道德上的——交互关系(reciprocity)。贯通作用(trans-action)不仅进行单向贯穿,而且是一种双向过程。既有作用也有反作用。把某些人视为能动者(agents)、把其他人视为受动者(patients)亦即接受者(recipients),尽管是一种方便的做法,但这是一种纯然相对的区分;没有不同时是反作用或回应的接受,也没有不同时包含了接受性要素的能动性。各式各样的政治法律哲学对于同意、契约、共识的强调,实际就是在承认社会现象的这一方面,尽管其表达方式颇具过度理念化的色彩。
相比作为社会过程构成要素的种种特殊作用,社会过程有一些稳定且持久的条件。人类肯定在每每做出的特定举止中形成习惯(habits),而体现在交互活动中的习惯就是习俗(customs)。依本文观点来看,这些习俗是法律的[唯一]渊源(the source)。我们不妨使用河谷、河水和河岸(banks)的类比或者(假如你喜欢的话)隐喻。与周遭乡土相连的河谷,或作为“地势”的河谷,乃是基本事实。我们不妨把河水比作社会过程,把它那多样的波浪、涟漪、漩涡等等,比作构成社会过程的具体行为。河岸是稳定而持久的条件,限制并导引着那可比作习俗的河水流向。与川流不息的河水相比,河岸恒久而且固定,但这恒久和固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地势中,河水是一股由高向低滔滔奔涌的能量,由此(当被视为一种既在时间上也在空间上的漫长过程时)形成并改造着自己的河岸。与特定举止相比,与构成过程的系列行为安排相比,社会习俗(包括传统、制度等)是稳定且持久的。但社会习俗以及作为其沉淀表述的法律规定,仅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它们或早或晚、或慢或快,要经受那些持续发展过程的磨损。因为尽管它们构成了持续发展过程的结构(structure),但它们在如下意义上是属于那些过程的结构,即它们在那些过程之内诞生并成形,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那些过程。
习惯和习俗给人类活动构造(constitution)引入的因素,是自称为经验主义者的早期哲学家所未考虑到的;这些因素一旦为人所留意,将深切更改我们对如下两类事物的需求:(1)外在于时间的法律起源和渊源;(2)外在于且独立于经验的标准或规范。就(1)而言,在反抗那些号称是不变且永恒的、不容置疑且不容变更的普遍物(universals)和原则时,早期经验主义哲学家往往碾碎了(pulverized)经验,并把经验中所有一般且持久的因素,化约为其所承载的各种一般名称。然而,每种习惯和每种习俗都具有特定范围内的一般性。习惯和习俗脱胎于如下两者的交互作用:(1)缓慢变化的环境条件;(2)人的利益和需要,它们同样在漫长时光里略生变化地大致保持下来。受篇幅所限,我无法对习惯和法律规则之间的各种关联进行充分定性。但显而易见、无需赘述的是:把习俗作为法律明文规定下来——无论该做法是如何发生的——将强化并常常拓展习俗那相对持久且稳定的特征,习俗的一般特征由此更改。
大家可能还不太看得出来,习俗和法律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构性条件,其一般性(generality)同聚讼不已的法哲学问题有何干系。此处要义在于,我们一旦承认社会现象的这一方面,从实践考虑便不必诉诸一种外在渊源(an outside source)。一个人可能基于纯形而上学的理论,继续蔑视时间,蔑视那些受制于时间条件的东西。但从实践立场来看,承认社会行动的某些成分有着相对缓慢的变化率,就足以完成一切有用的、一切实际需要的工作,这类工作在过去以及在其他文化氛围中,导致各种外在渊源的确立,例如上帝的“意志”或上帝的“理性”、中世纪理论里面和(格劳修斯及其后继者那样的)哲学家笔下的“自然法”、卢梭的“公意”、康德的“实践理性”。
上述看法不适用于“主权是[唯一]法律渊源”这一学说。“主权”所指称的东西,至少具有社会事实的性质,存在于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之内(而非之外)。这种观点曾经备受政治学和法理学研究者瞩目,现在却已风光不再——倘若我没有弄错的话,该事实表明为何只需对其进行扼要阐述便足矣。(倘若我不是错得很离谱的话)该观点已多少有些迂腐陈旧了,我们甚至很难想见它为何曾盛极一时。细察之下,该学说的力量之源有二。(1)它避免使法律取决于外部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渊源,代之以能够获得可证实(verifiable)经验意义的条件和能动性。(2)主权是个政治术语,该学说之风行适逢通常所谓“政治”领域出现的立法活动大爆发。奥斯丁式的(Austinian)法律渊源理论,可以说是用理性化的方式赞许如下运动:将法律规则和法律安排纳入审慎目的性行动(deliberate purposive action)的范围,牺牲掉司法判决所解释的习俗的相对无计划结果(comparatively unplanned results)。该学说原本的魅力大都已经丧失,因为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趋向于使主权顶多作为众多社会力量运作的表达,弄不好则是纯粹的抽象物。基于主权的法律渊源学说代表着一种转变,即从接受外在于社会行动的“各种渊源”,到接受内在于社会行动的某一渊源,但该转变固守单一社会因素,并把它孤立冻结起来。一旦人们发现,社会习俗和(一定程度上)社会利益,其实凌驾于任何一群能被挑选出来并称为“主权者”的特定人,主权学说便消沉衰落了。联系经济因素来解释政治活动的趋势不断增长,自与前述情况殊途同归。
目前为止还没谈及目的和标准。人们可能会说,假如接受我关于经验性法律渊源的论述,则只会更加支持外在于现实社会活动的目的与标准。因为据说凡此种种习俗与法律的壮大,并不表明它们应该存在,亦即并不是它们价值的检验标准。简言之,我们在此面临着“与事实相关的价值”(value in relation to fact)这个大问题,以及许多人持有的一种立论:事实与价值是截然分离的,故而,存在物的评价标准,须以任何可能的经验领域之外的标准为其相应渊源。
就此而言有着根本意义的是,承认作为连续活动的社会事实是持续发展着的。假如作为社会事实的那些东西,因被视为封闭的和完全终结的,而被我们切割下来,则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认为,社会事实的评价标准必须外在于现实存在物的领域。但假如社会事实是持续发展着的,则它们产生各种后果,而对后果的考虑可以提供某种理据,便于我们决定应否改变社会事实。
假如不把社会事实作为发展着的事务,则在理论上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一种外在的目的和标准,——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有充分理由认为,此类标准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状况,毕竟按照定义,此类标准与现实社会条件无关。不可否认,在既往的不同时空下,人们曾经持有和使用彼此冲突的不同标准。它们的冲突充分证明,它们并非源自任何先天的绝对标准。若不承认可从现实社会活动中抽取标准,其实就等于否认绝对标准的影响或效果(即便真的存在绝对标准)。有什么理由认为,诉诸非经验性的绝对目的(a non-empirical absolute end)的那些人所提出之标准,会与过去提出的种种标准命途有别呢?
应付这类难题的通常方式,是承认必须区分形式(form)及其内容或填充物(contents or filling),形式是绝对的,内容或填充物是历史的、相对的。承认这一条,对绝对目的学说旨在迎合的所有东西都是致命的(fatal),因为一旦承认,则一切具体价值判断都必须立足于所谓经验性的、时间性的东西。
按本文的观点,标准存在于后果中,存在于社会上持续发展着的东西的功能中。该观点若被广为接受,势必把理性(rational)因素大规模引入法律安排的具体评价。因为该观点要求我们凭借能够获取的最佳科学方法和材料,运用理智去探究法律规则、法律判决和制定法的各种后果,并且在探究时关注现实情景的语境。当前的趋势——即在探讨法律问题时回归其具体社会情境,而非流连于问题与问题之间关系的相对真空——迄今还只是初露端倪,但将因一以贯之的法律理论而得以强化。再者,社会事实是持续发展中的事务,一切法律问题也都在这些持续发展中的事务之内各得其所——若这两条在实践中获得系统认可,则如下事情的可能性将比现在大得多:获得一种新型知识,从而能够影响那永无止境的判断标准改进过程。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