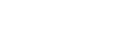乌齐格里.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又字艮斋,蒙古正红旗人,晚清大臣、理学家。
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北京政变后,他以讲程朱理学受到清廷重用,擢为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同治皇帝师傅职。作为“理学名臣”、“三朝元老”参预朝政,在清末的政界和学界都充当了重要角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治十年(1871年),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因病再度乞休。不久病逝,追赠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倭仁政治态度保守顽固,为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所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
人物生平
潜修理学
倭仁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先辈是驻防八旗中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中下层旗人社会。倭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驻防地开封度过的。 道光九年(1829年),倭仁中进士,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选庶吉士,被授为编修,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 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乡。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集会,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年),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做官,倭仁和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都聚集在了他的周围。唐鉴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自从向他问学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向,弃王学而改宗程朱,终身笃信程朱理学。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此时得识倭仁,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订交后,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曾国藩对倭仁的理学修养工夫很钦敬,也学他的样子写日课,彼此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与弟书中称倭仁为“令人对之肃然”的“益友”。就这样,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与推崇,从而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取得较高的地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提拔为詹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迁移为大理寺卿。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鉴告老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的重要支柱。
出佐文宗
道光三十年(1850年),文宗咸丰帝即位,为振刷纪纲,励精图治,诏谕内外大小官员工上书陈言,献计献策。时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经纶满腹,企图一展抱负,特上《应诏陈言疏》说:“国家行政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用人又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和小人都是难以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但是他们做的事却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看大抵都是君子拙劣,而小人善于逢迎;君子为人处世稳定,而小人善于摇摆;君子爱惜人才,小人大多排挤与自己政见不一之人;君子都图谋远大,以国家的发展为先,而小人大多只看眼前,以聚敛财物、刻薄待人为己务。遇事刚正不挠、无所阻挡的人,那才称得上君子;善于逢迎、工于趋利避害的人,都是些小人。所以,以皇上的聪明之资,肯定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之。君主掌握了用人之术,才能国家大治。”咸丰帝看了他的奏疏之后,称赞他敢于直言,于是晓谕大小臣工以倭仁为榜样上疏进言 。不久,礼部侍郎曾国藩上奏了用人三策,咸丰帝看了之后又想起了倭仁先前的奏疏,于是起草了同样的话给予勉励 。
接着,清廷授予倭仁副都统衔,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上疏说倭仁充任帮办大臣是大材小用了,咸丰帝说:“叶尔羌帮办大臣是边疆要任,不是闲散的职位。如果只将外任官员上迁,那岂不是有违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的大政方针吗?” 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马上任。尽管倭仁对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毕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远在叶尔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对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
宦海沉浮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倭仁有鉴于咸丰帝即位以来政治上毫无起色的情形,从叶尔羌上《敬陈治本疏》,大谈“治本”之论。倭仁所谓的“治本”是要“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这仍是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出自理学家的倭仁本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对于被太平天国运动搅得日夜不得安宁的咸丰皇帝来说,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咸丰皇帝看来,倭仁的“治本”之论当然并非不对,只是这些“统论治道”不切实务的“空言”,实在无助于当务之急。
咸丰三年(1853年),倭仁弹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任意摊派路费以及护卫索赃等几款大罪,清廷下诏训斥他没有经过确认就上疏弹劾,任意参奏,于是将其下部议罪,降三级调用。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叶尔羌或许本就不该有的无奈生涯。 咸丰四年(1854年),侍郎王茂廕等请命派倭仁会同筹办京师团练,咸丰帝因为军务并非他所长,未同意他的建议。不久命倭仁以侍讲候补的身份入直上书房,教授惇郡王读书。 咸丰五年(1855年),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咸丰七年(1857年),又调任户部,管理奉天府尹事,又上疏弹劾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署理盛京将军。在盛京的任职,不仅使倭仁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官场处事经验。其政治阅历和经验逐渐成熟,提出了昔人论政曰:“尽心,平心。尽心、忠也、平心、恕也。人为政为学一以贯之矣”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倭仁作为朝廷的使臣出使李氏朝鲜,颁布咸丰皇帝去世的“遗诏”和同治皇帝登极的“恩诏”,这预示着倭仁的政治生涯开始出现转机。
同治元年(1862年)元年,倭仁升任大学士、官拜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因为倭仁老成持正,并且学问优长,特命他作为同治帝的帝师。倭仁缉查古代圣贤帝王的事迹,并且搜集古今名臣飞奏议,整理之后进献给同治帝,被赐名为《启心金鉴》,放置在弘德殿作为皇帝学习的教材。因为倭仁素来严厉持正,所以同治帝对其尤为忌惮。七月,任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任大学士,兼管理房部事务,旋授文渊阁大学士。
同文之争
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场争论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京师同文馆成立于 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五年(1866年)底,恭亲王奕訢等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拟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和该各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学生,由总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馆教习。殊不知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在恭亲王等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顺利实施之时,反对派已在酝酿抵制。同治六年(1862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奏折揭开了这场大论争的序幕。张盛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可是,张盛藻毕竟人微言轻,他的奏疏遭到同治帝谕旨的严厉训斥。
张盛藻的意见被压制后,倭仁亲自出场,随即卷入论争之中。他与恭亲王奕訢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他从立国之本的高度立论,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地步。以倭仁的学养与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倭仁上奏的当天,两宫皇太后即召见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訢等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重申增开天文算学馆以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月十九日,奕訢等人上奏承认:“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显得底气不足了。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的把柄,对倭仁反戈一击,要倭仁“酌保数员”,另设一馆。这个建议得到谕旨允准。这下可为难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据实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难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还谕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至此,双方争论已到白热化程度。朝廷的故意为难已使倭仁狼狈不堪,而奕訢等人在朝堂上的当面围攻更使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几经折腾,倭仁终于气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倭仁与奕訢等人的正面冲突就此平息。
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在此过程中,倭仁以“本末”论和“夷夏之防”的观念为思想基础,否定西学的价值,从而认为向西方学习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有导致中国文化沦亡的危险,充分显露出倭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
晚年逝世
经过同文馆之争的打击,倭仁失去了部分兼差,但他仍以大学士的身份在弘德殿行走,可以更专心地做同治皇帝的师傅。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初八日,十四岁的同治皇帝“开笔作论”,师傅们出题为《任贤图治》,皇帝写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同治所述,和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完全一致。同年,醇郡王奕譞奏请同治帝在太后召见群臣时“升座听政”,即见习临朝听政,得旨允准。
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总理衙门又以向列强屈服告终。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倭仁认为:“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可见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光绪八年(1881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人物评价
·《清史稿》:“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於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
·晚清理学大师唐鉴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晚清名臣、理学家曾国藩评价:“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
·桐城派名家方宗诚评价:“公(倭仁)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劘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久而弥精,老而愈笃,名益尊位益贵,而下学为己之功益勤恳而不已。”
·时人评价说:“(倭仁的日记)质之天人而无愧怍,传之后学可为典型。”
·晚清学者吴廷栋评价:“艮峰先生乃躬行实践之学,读日记而学其省察克治,即是奉以为师。”
·倭仁同年朱兰(久香)评价:“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
·李棠阶评价:“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胡,内推倭、李。”
思想主张
哲学思想
·认识论
倭仁在认识论上主张“ 理在心中”的先验论。《为学大指》说:“盖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不会自明,因为有“物蔽”,人们为“利禄之趋,习俗之徇,泪没沉沦,而为人之理遂失”。因此,需要“致知”,认识天理。这对任何人都一样,圣人也不例外,世上人人都应当学习。倭仁认为认识天理即是认识己性、人性和物性,并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阶段:
①“尽己性”,即认识自己的天性,按天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私念。因为“念虑萌动之初,为善恶分途之始”,不去掉私念就不懂得自己的善性。去念的办法是“端庄静一”、“涵养本原”、“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只有这种内心修养,才使天理不受物蔽而清明昭著。
②“尽人性、尽物性”,即认识人们之间和物之中隐藏的天理 。穷尽物理要从一物上穷理开始,“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更重要的是用“类推”的办法,认为类推可认识到大至“天地之运,古今之变”,小至“一息之顷,一尘之微”的万物都是一“理”类推还能认识到“物我一理”,自一身,以至一家,至于万物,都有君臣、朋友的关系,都是一个天理。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尽己性才能尽物性,否则就不能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物性是己性的类推。他指出那种从万物中寻找离开己性的“闻识”“晓会”是对穷理的曲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尽己性必尽物性,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应把尽物性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他指出,因“物我异体”而只修己性,不及人和物,是不懂己性的真正含义。倭仁在社会问题上主张“帝王心治天下”的唯心史观认为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朝廷的政治和用人,政治和用人又受帝王的心制约。《辅弼嘉谟》说,帝王的心“为万事之主”,是“用人行政之得失”的原因,“天下之治乱安危系之此”。帝王心正,则天下事没有不正的;心不正则不会有正的。他要求帝王之心“明白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做到“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象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治理天下。
·伦理思想
倭仁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是其一生治学、为官,悟守并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必然结果,其体现了儒家“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的道德价值观。同时也生动地演绎了儒家伦理思想在一个少数民族士大夫身上的璀璨绽放,这也足以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教化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功用 。
倭仁伦理思想的基本概念是“ 理”,其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等传统道德。倭仁认为人自身有仁、义、礼、智之理,人们之间的理不异于己之理,物'之理不异于人之理,把世界万物和人伦关系都统一于这个“理”之中。倭仁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为学大指》一文中,概括为六个要点,即“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歌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系统地阐述了治学的宗旨、目的、内容、方法及效用等重要问题 。
理学思想
·创新程朱理学
倭仁认为,程朱理学是十全十美、万古无弊的圣经贤传,是“至精且备”、博大精深的“正学”。程朱以外的各种学问,不是异说末学,便是左道旁门,都不能藉以达到超凡入圣的目的 。倭仁理学思想的王学渊源,从其理学思想本身也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印证。这对倭仁的理学宗向有重大的影响,使倭仁的理学思想具有王学的渊源。
程朱理学中的道德论备受倭仁推崇。在他看来,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变化无不受由人的“心身”所引发出的道德关系所包括,所支配。程朱把万物归源于“性理”,而倭仁则归结于道德。“诚”、“敬”本来是理学道德论方面的两个范畴,倭仁不仅称之为道德论中的最高原则,而且把它们上升到宇宙观的高度,与“阴”、“阳”相提并论 。
对程朱理学,倭仁虽然没有理论创新,但他力图按照程朱的观点阐释了一些重要的理学范畴与命题,构建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
首先,在理气论方面,倭仁以 “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说:“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终,无非此理。”在倭仁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理气”生成,所谓“天地祇此阴阳之气,健顺之理,吾与万物同得此理气以生。”关于理气先后的问题,倭仁的思想与朱熹相似。朱熹主张理气本无先后,如果一定要分个先后,则是理先气后。朱熹的理先气后思想,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理是“逻辑”上在先,而不是简单的时间上的先后。朱熹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天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可见,朱熹所说的理在气先是就世界的本原而言的,其逻辑在先说表明朱子哲学基本问题中理是第一性的。
其次,在心性论方面,倭仁按照程朱的观点阐释了理学心性论的一些重要范畴与命题,如心、性、道心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已发未发、天理人欲等等。人的感性情欲不加控制则流于恶,所以“危”;人的道德良心潜隐在内心深处,与情欲混杂,微妙难见,所以“微”。明乎此,用道德良心统率感性情欲,则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精神境界。至于道心是什么和人心是什么的问题,倭仁通过否定明代理学家罗钦顺的观点而稍微作了一点符合朱子哲学的阐述,他说:“整庵谓:‘道心是性,人心是情。’心窃疑之。道心如恻隐羞恶之属,原于性命之正,而非即性也;人心如耳目口鼻之欲,发于形气之私,而不得谓之情也。”倭仁认为道心不是性,人心不是情。道心是合于道德原则的知觉,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人心则是以个人情欲为内容的知觉,是指人的感情欲念。这颇与朱子的观点相类似:“只有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又如,源自《中庸》的“已发未发”又称“中和”,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已发未发是理学心性论的重要范畴,按程朱学派的观点,已发未发是指人的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已发指思虑已萌,未发指思虑未萌;未发指性,是心之体,已发指情,是心之用。
再次,在知行观方面,格物致知、居敬穷理、涵养省察等,这些以“知行”为中心的范畴与命题是程朱理学的重要修养方法。格物是《大学》八条目之首,格物致知是修齐治平的基础,朱子哲学对此非常重视,故朱子曾经特为格物“补传”,这一事实被后世程朱派理学家认为是朱子在理学上的重大贡献。倭仁也有同样的认识,他说:“格物不得力,第一关便隔碍了,下面节节都是病痛。朱子补传,洵有功万世。”主敬是程朱理学提倡的一种重要的心性修养方法。倭仁说:“心主于敬,无少放纵,然后至虚至灵之中,有以穷夫酬酢万变而理无不明,盖未有不居敬而能穷理者。”在倭仁看来,主敬就是心不放纵乱思,保持一个虚灵的心之本体,不受外物的干扰而自然体认天理,达到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知先行后,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倭仁说:“力行尤以致知穷理为先。”他认为,“知”即是孔孟之道,道理已经程朱辨明清楚,后人只要按程朱之学去做即可,要做这“行”的工夫,必须努力将获得的点滴知识随时付诸实践。“孔孟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在人的个体道德修养方面,有了道德知识与观念,认识了道德原则,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这样就能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
从倭仁理学思想本身来看,自从转向程朱之后,他确立了严格的“尊朱”的学派立场。为了表明这种“尊朱”卫道的立场,倭仁力图按程朱学派的观点阐释了一些重要的理学范畴与命题,甚至直接征引了不少程朱理学家的言论以阐述他的理学思想。倭仁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符合程朱理学精神的,可谓比较地道正统的程朱派理学,“倭仁之学虽不敢言及孔孟程朱,然能诵其言守其法,躬行实践。”正如时人所说乃“孔孟程朱之真传”,是“程朱之正脉”。可见,倭仁当时已以正宗的程朱理学家闻名于世。
·王学思想
倭仁在他的《日记》中说:“事天无他,事心而已矣。 ”可谓一贯王学精旨,把心即理的王学命题一语道破。另外他还在《日记》中谈到“看未发气象”时直接征引王阳明的话,他说:“看未发气象,姚江有一段说得紧切,云:此是教人用戒谨恐惧工夫,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洞洞属属不知其他。'即程子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之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条:“延平每教人静,其云:学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须打断诸路头,静中默识,使泥滓渐渐消去。又云:静坐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不惟于进学有功,兼亦是养心之要。又每言脱落融释。皆吃紧为人语。 ”静中体验未发,是理学中二程高弟杨时再传至李侗(延平)的所谓“道南指诀”。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他曾经教朱子静坐体验未发气象,即通过高度沉静的内心修养而体验一种浑然与物同体的神秘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直觉主义的修养方式。尽管朱子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始终未能获得那种体验,因而很自然地对静心体验作为道德修养的普遍有效性表示怀疑,而最终倾向于程颐“主敬致知”的理性主义修养方式。正如吴廷栋的指责,倭仁所赞许的延平静坐法“毕竟非学者通法”,其与程朱“主敬”法相背,反为“谈姚江之学者所假借” ,其实,吴廷栋指出了倭仁理学思想中的王学根底。
政治思想
对于“治道”的关怀,倭仁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吏治上。居官尸位易沾染名利习气,利欲使人堕落。倭仁认为为官第一要务应是“将名利心打叠净尽,方能笃实光辉” 。将一己的“名利之心打叠净尽”,发而为政,倭仁则主张居官应仁民爱物。他在答仓子益时曾经说道:“唯有克己爱民,事事为百姓计,不为一身计。凡百举动皆服草野之心,则官民一体相联,即可以消内变,亦足以御外侮。” 只要官民同心同德,何愁国事不兴。实现官民一体,居官就要通下情。
针对当时吏治弊坏之风,他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朝廷应认真整剔,实力振刷,杜绝请托之风。二、对州县官员应实行奖赏与惩罚制度。三、制定检查制度, “大吏察州县,朝廷察大吏”。这样一来“民困可苏,民心自固,寇乱之源亦由是可弭矣” 。
家族成员
儿子
·长子:福咸,拔贡,历任孟津县知县、江苏盐法道、署理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1860年),与周天受一起战死于宁国,赏骑都尉世职,入《清史列传》忠义传。
·次子:福纶,曾任广东候补同知、郎中。
·幼子:福裕,官至奉天府府尹。
侄子
·福润,官至安徽巡抚。
·福曜,倭仁之侄。
孙
·衡峻,福咸之子,曾任户部员外郎。
·衡瑞,福咸之子,钦赐举人。
史书记载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一.列传一百七十八》
历史地位
唐鉴京师讲学期间,倭仁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其后,倭仁不但自己潜修实功,而且以其学养和地位力图将士林社会导向正学之途,并不断地为纯正程朱理学的道统和学统而努力。“肩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倭仁以理学道统的传承人而成为道咸同时期倡导程朱理学的重镇。倭仁的理学地位与声名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是由各种原因与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师友的推崇。道光末年,在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诚如曾国藩所言:“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无疑,论资历学识,道德文章,唐鉴都堪称当时第一理学家。德高望重的唐鉴很欣赏倭仁,他曾对曾国藩称赞倭仁“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吴廷栋也曾对人自称“心折”倭仁之“笃行”,甚至在咸丰皇帝面前声称“尤佩其笃实”。曾国藩与倭仁更是相交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可见,在当时的京师理学群体中,倭仁已有相当高的学养地位。道光二十六年,唐鉴告老离京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重镇。有人评论说:“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对倭仁的理学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次,弟子门生的宣扬。倭仁的理学地位既在师友中得到认可,同时,其理学声名又在众多的弟子门生中得以流播。倭仁多次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读卷、阅卷大臣之类的考职,据统计达十八次之多。科举考试是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阶,考官与考生之间的所谓“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是传统社会中的一张厚重的人情关系网。“乡会试中式者,对于主考、房官例称师生,其风自唐、宋来相沿已久。……明代师生门户之风尤盛,清代亦然。”举人、进士不但于主考、房官有师生之谊,而且“与夫本科监试官知贡举、监督等,推之复试、朝考、殿试,凡派为阅卷者,无不认为师生”。倭仁历任多种考职为其名望地位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科举考试的名分上说,倭仁可谓门生遍天下,如叶名琛、何桂清、彭蕴章、朱琦、罗惇衍、袁甲三(以上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倭仁为同考官),甚至胡林翼(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倭仁为同考官)、张之洞(同治二年癸亥恩科,倭仁为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都出自倭仁门下。虽然无法厘清他们之间的具体交谊关系,但是,这种师生名分当是客观存在的。太平天国时期,倭仁为同考官的道光乙未科进士陶恩培、孙铭恩、吕贤基、罗遵殿“先后殉粤寇之难,世称倭门四忠”。所谓“倭门四忠”之称,其实正是对倭仁声名的宣扬。
倭仁“诱掖后进不倦”。从所见的有限史料,也可以看到倭仁通过他的弟子门人影响社会的情况。这里仅举于荫霖与沈源深为例。于荫霖,字次棠,号樾亭,吉林伯都讷厅人。咸丰九年进士,官至河南巡抚。据记载,同治初年,于荫霖官翰林时,“倭文端公为理学名臣,公相从问学”。“通籍后从倭文端公受省身克己之学”,“一以朱子为宗”。于荫霖虽长年为官,然仍潜心理学,据史载:“荫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虽已贵,服食不改儒素,朱子书不离案侧,时皆称之”。沈源深,字叔眉,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沈源深尝“从乡先辈倭仁学”,后为福建学政,“以化民成俗为己任,颁行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陈宏谋《豫章学约》,并自述《劝学浅语》,训迪多士,奏请先儒游酢从祀文庙,位在杨时之次,闽中正学为之振兴”。可见,倭仁奖掖后学,即使其理学声名得以广播,也使正学在社会上得以昌明。
另外,早年在京师曾从倭仁问学的后学涂宗瀛 与洪汝奎,晚年都致力于刻书,倭仁文集《倭文端公遗书》和倭仁、吴廷栋校订的《理学宗传辨正》两书的初刻本都是由涂宗瀛的六安涂氏求我斋刻印刊行,后又都被洪汝奎辑入《洪氏唐石经馆丛书》,这些工作无疑有助于促进倭仁对社会的影响。
再次,理学名臣地位的影响。道咸时期,倭仁即以理学名于世。同治年间,倭仁飞黄腾达,位极人臣,成为一代理学名臣,其时,倭仁任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同治帝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谓“首辅、师傅、翰林掌院、户部总理,皆第一清要之席”。这种理学名臣的地位使倭仁成为当时士林社会的人伦表率,诚如曾国藩所说,乃“当世仪型,群流归仰”。以至于倭仁逝世时,翁同龢禁不住感叹:“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 ”可见,倭仁在当时士林社会中的泰山北斗地位,难怪《清儒学案》称之为“道光以来一儒宗”。为倭仁在晚清儒学(理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