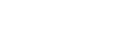我的母亲程先枝,生于1941年11月27日,逝于2023年3月11日(农历二月二十),在这世间走过了82个春秋。
3月11日那天清晨,天降小雨,母亲窗外的那棵老杏树粉白色的花瓣洒落一地。苍天垂泪,落花有情,似乎为母亲送行。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天会成为母亲生命的终点,从早上起,我就翘盼着爱人带着孩子从合肥早点出发,早点到家,早点让母亲看到自己两个可爱的孙子。
事后回想,母亲是有某种神秘的预感的。3月9日一早,母亲就让大姐、小妹为她擦洗身体、换新衣服,忙乱中大家一时没有找到新袜子,母亲动动脚、努努嘴,以示不满。尽管如此,我仍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心底不愿承认生死离别时刻的逼近。我反复告诉母亲,儿媳和两个孙子周末回来看她。
母亲坚持了两天,爱人和孩子上午10点多到家时,她的神智是清醒的。王旻浩和王晨浩喊着奶奶、抚摸着奶奶干枯的手,她已经不能睁开眼睛,但嘴角在颤动,知道孙子们回来了。三个多小时后,下午1时30分许,母亲进入弥留之际,被扶上“寿椅”、手“持”拐杖,在儿女们、孙子们的陪伴中离开了这个她深深爱过的世界。如果最后时刻她老人家还有意识的话,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不舍的,守望着子女后代们幸福生活,是她留恋生命、热爱人间的唯一理由。从母亲嘴角隐隐含有笑意的端庄神情看,她又是安详、知足的,用信佛的大姐的话来说,母亲是结了仙姑的缘。
母亲能活到八十余岁,可以说是个生命的奇迹。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父亲把她的棺材和香纸都准备好了,懵懂的我好像也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一个人在河边凛冽的寒风里独自伤神了很久。但那次,母亲活过来了,死里逃生,我们仍是有妈的孩子。母亲在24岁生大姐坐月子期间,受风寒加上吃不饱,得了在当时没钱治、也治不好的肺结核。那时所谓的治疗,也就是村里赤脚医生上门打针、吊水,有两次用错了药,母亲奄奄一息、死去活来。有一次母亲的病实在严重了,父亲和村里人把竹床做成担架,抬着母亲去十几里外的牛集医院,半路上母亲渴得很,就在一个村口停了,父亲进村想讨点开水给母亲喝,但村子里人知道母亲得的是令人色变的肺结核后,都躲得远远的,父亲无奈,只能含泪手捧池塘里的凉水给母亲喝了。病痛折磨母亲一生,母亲的身体始终是羸弱的。在母亲70岁那年,我终于把她接到合肥住居,有一次她瞒着我,让干儿子带她到医院检查,不查则已,一查医院立下了病危通知书,肺部钙化了三分之二,住院治疗几个星期后,医院也无能为力、不了了之。这次检查和住院,让我这个不孝之子认识到,母亲的身体原来时刻处在医学意义上的病危状态,母亲完全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对子女的深爱迸发出坚韧的生命力。
展开全文
母亲的一生,是多舛多难的一生。除了病痛的折磨,她经历了青年时丧失双亲、中年时痛失伴侣、老年时两次遭遇飞来横祸(67岁、77岁两次车祸)、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四进四出医院(闯过脑梗、新冠、癫痫三道生死关)。这些磨难,叠加着岁月的沧桑,把她的腰背早早压弯成了一道山梁,但没有压垮她的意志。1993年仲夏,我和母亲在安庆市立医院照料生病做大手术的父亲,父亲的病情不明朗、医疗费没着落、天气酷热等一系列因素,让母亲支撑不住了,发起高烧。午后,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外,万般无助、高烧难耐的母亲,匍匐在我身边,抱着我的双腿,不停地亲吻着我右腿膝盖处的胎记,滚烫的泪水顺着我的膝盖流淌,分不清是母亲的还是我的。这是我记忆中,她唯一一次亲吻我,肆意流露出对儿子的爱恋与依赖。那一刻,我是她最强的精神支柱;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与病痛、苦难伴随的必然是贫困、艰辛,母亲的一生,是操劳辛劳的一生。母亲是庐江县泥河镇程老屋人,20来岁丧失双亲,族人做主要把她嫁给当地一户人家,母亲不愿意,偷偷跑了出来。母亲一路拾荒乞讨,流浪到了几十公里外的枞阳县浮山乡,被好心人收留后作媒嫁给了从小就是孤儿的父亲,两个孤苦伶仃的人似乎缘分天定,从此相依为命。据说,他们成家时,临时搭建了一间茅草屋,筷子是用树枝削成的,碗里能装什么,就可想而知了。生几个姐姐坐月子时,母亲也要到地里干农活挣工分,有时只有红薯做主食。母亲曾回忆:生二姐坐月子时,家里一丁吃的也没有,她饿得奶水都没有了,邻居大娘赊了半升米,她熬成大半锅稀饭一口气全部喝完,吧嗒吧嗒嘴巴还觉得没饱。父亲和母亲,起早摸黑,兀兀穷年,从一穷二白、家徒四壁的茅草屋里,把我们5个子女拉扯长大、养育成人,甚至还能供我读书上大学,其间的千难万苦、含辛茹苦,我们作为子女所知者不足百分之一二,只有大姐的记忆更多更深些。我能记忆的一个永恒画面,是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衣裳、纳鞋底,手指被针扎出了血、母亲用嘴舔舔手指的那一瞬间。
贫苦辛劳的生活,养成了母亲极其勤劳、极其节俭的品德。一天没有歇息,一分钱不舍得为自己花,一粒米掉在地上也要捡起来。在合肥生活期间,起初母亲如鸟在笼,浑身不自在,只能在阳台及门前空地上想方设法种点蔬菜,后来她发现其他老年人捡垃圾能挣钱,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从此每天早出晚归,乐此不疲,甚至后悔知道得晚了。每当数着卖垃圾得来的三五块钱时,母亲的脸笑得开了花,她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人。2018年不方便捡垃圾后,母亲很是寂寥与失落,便不停地吵着要回老家。此后的几年间,母亲回到了自己呼吸舒畅的家园,在菜地里劳作不辍,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我们打电话劝她吃好些时,她说:“我忙得哪有时间做吃的?!”在学会寄快递后,她忙得更欢了,动辄把几十斤的南瓜、冬瓜、红薯快递到合肥。我们说,邮寄费比买这些东西还贵,那也阻止不了她给儿孙邮寄自己劳动果实的热忱。
艰难困苦的生活,养成了母亲独立、要强的性格。即使在合肥生活期间,母亲到社区医院拿药、吊水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78岁那年,她突然想到庐江娘家去看看她的姐姐,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自己坐公交车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探亲,跑到姨娘家,却是铁将军把门,她独自在乡间公路辗转蹒跚了十几公里,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找到姨侄女家。2022年12月感染新冠,在ICU抢救一个多星期后转到呼吸科,母亲还躺在病床上就开始锻炼。春节期间我们担心她行走不稳,母亲坚持要自己独立上下了几节台阶,以证明自己能行,此时的母亲逞强得像个孩子。
要强的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子女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苛责,期望我们过得不比别人差,为此她会唠叨不止、呶呶不休,骂起人来粗俗尖刻,以致青少年时期的我很有些为她难为情,却不知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内心柔软善良。厚以待人、薄以待己,是母亲一贯的个性。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做新房子,上梁仪式后,母亲用围裙兜着糖果花生之类的分发给大家,我也很想吃到一块糖果,与村子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挤在母亲面前,母亲却对我始终视而不见,把数量有限的糖果全部发给了其他人。我当时的不解与失落,至今记忆犹新。听村里老人说,十几岁的我与母亲顶嘴:你就知道把别人吃得胖胖的,把自家人饿得瘦瘦的。这句话成为多年后村里老人见到我时的笑谈。
母亲的生活,当然不全是苦难,也有欢乐和幸福的时光。在我看来,好面子的母亲大约有三次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次应是我1989年考上大学,成为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母亲虽然没有喜形于色,但无疑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的。第二次应是2005年添孙子,重男轻女的母亲乐得喜笑颜开、逢人就讲,春节舞龙灯,特意请龙灯到家举行了一个祈福仪式。第三次是80岁生日时,大姐她们为母亲张罗了一个风风光光的生日,大宴亲朋邻里,母亲很享受这份热闹和儿孙满堂、葳蕤繁祉的祥和,以至于今年春节前,行动已不便的她还吵嚷着要再宴请一次亲朋。
作为妻子和儿媳的母亲,她从未忘记自己的本分与责任。我的父亲生病卧床三年,其间母亲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千言万语,难以诉尽。子女们生活初步好起来后,母亲想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父亲修个像样子的墓,这是她埋在心头十多年的心愿。及至2021年冬至前夕,母亲突然又提出要为我的爷爷、也就是她从未见过的公公修墓立碑。我们都觉得她是心血来潮,但还是按照她的意愿为爷爷修了墓、立了碑。现在回想起来,母亲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深谋远虑,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尽到她作为儿媳的一份责任。
自父亲去世后,无论母亲在老家还是在合肥,我能有效陪伴她的时间,每年不过三五天,晚上闲坐下来,母亲东家长、西家短,说些旧人旧事,我或坐或来回踱步,对她讲的内容不甚上心,但也听得津津有味,思绪飞回到童年,真正体味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些美好的时光,太短暂太短暂,再也回不来了!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对母亲的强烈依恋,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我大约五六岁时,那天傍晚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天色渐黑,我越来越孤单害怕,便壮着胆子走到村北口的小孤坟那里,远远对着在菜地里忙活的母亲大喊:奶奶,你快点回来!母亲慌不迭地收拾,挑着空粪桶回来了。另一次是2010年夏天,在经历了连续一周的高强度工作后,疲惫的我心底突然涌出找母亲倾诉的渴望,便驱车来到母亲的住居,可她不在屋里,左等右等,我怅然而归。近些年,我经常怀念起母亲做的糖炒黄豆、糖炒花生米、糖炒小汤圆、蚕豆米蒸鸡蛋、豌豆咸肉糯米饭等儿时味道,只要我流露想吃的意思,母亲就像领到一件神圣的任务一样,总是超额完成,看着我吃她做的饭菜,母亲的眼里流淌出无限的满足。母亲回老家后,我又能吃上母亲腌制的咸鸭蛋,独特的臭香味,是母爱与时间一起酿出的美味。这些母爱的滋味,太珍贵太珍贵,再也吃不到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一位普通的中国式母亲,古往今来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母亲中的一员。她的全部世界只有家庭,她的全部牵挂只有儿女,她的全部付出只为家庭儿女,这样的爱绝不是自私的,而是“无我”之境,是滋养人间的大爱,是天下母亲共同的大德。我的母亲,她经历的坎坷磨难也许比同龄人略多,但她对命运的安排从无抱怨、从未认输。“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母亲不懂这样的道理,但她很好地做到了。
与病魔斗争了将近60年,母亲您已创造奇迹,启迪我们以生命的坚强与坚韧。
为我们辛劳了将近60年,母亲您已经太累了,您放心地休息吧,我们会薪火相传。
与父亲分别也有28年了,你们也该再相会了,你们会像往日一样相亲相爱过日子。
我的母亲,永远的母亲。
--END--
来源:文乡枞阳
转载请注明出处,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王武伟安徽枞阳浮山人。硕士,1993~2003年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2003年,创办安徽省创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法人。
相 关 链 接
文乡情怀|一根黄瓜
鍾建勋|母亲
汪双庆|回忆我的母亲
陶继平|农民母亲与她的四个研究生儿女
许耀明|怀念母亲
徽庐|我的母亲不温情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