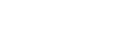天涯微信号: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com
《天涯》2023年第2期
每一处“边地”都是当地人心目中的“中心地带”,正所谓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本期散文小辑,内蒙古的裴海霞记述荒野牧人的家族传奇,新疆的刘予儿寻访建造永恒之所的奇人,云南的李达伟在岩画上汲取向死而生的力量,甘肃的刘梅花讲述了一个浪子从冬窝子回到夏牧场的历险记,寄身武汉的千忽兰则追忆着新疆那些与自己命运相关的符号。
今天推送李达伟《岩画》,以飨读者。
点击封面,一键购买
岩画
文/ 李达伟
一
苍山中的岩画和苍山中的某个庙宇中见到的壁画,都是残破的,都被时间侵蚀和篡改。一个是天然的石头,另一个是建筑的墙体;一个是在敞开的自然空间里,另一个是在相对封闭的场所内。我们抬起了头,岩画在悬崖之上,精美的壁画被画于建筑的中央,作画者的姿态将与我们看的姿态相似,那是需要仰视的岩画和壁画,也似乎在暗示我们那是需要仰视的美。岩画,色彩天然而单一,线条粗犷而简单。壁画,线条细腻,色彩华丽。岩画与壁画,呈现给我们的近乎是两个极端,从最原始的简单慢慢发展到无比精致。在苍山下,我们谈起了文化的发达会带来对美的极致追求,但有时也会走向极端,会走向追寻病态的美。壁画上人物的精美与圆润,色彩的华丽,是美的极致呈现。我们庆幸,在那里美的病态感并没有出现。
展开全文
我在那个天然的空间,看岩画。它们在时间的作用下,变得很模糊,模糊成了它们的一种外衣。我们所见到的那些色彩,同样是它们的一种外衣,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时间带来的一些错觉。岩画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自然之所,有高山草甸,有多种植物,有种类繁多的杜鹃。在岩画之下,现实退散,幻象出现。我们确实只能猜测那些在洞穴中在山崖上作画的古老艺术家,是在怎样一种原始的冲动下开始作画,并完成了一幅又一幅拙朴简单的画。我在岩画前想象着那些原始艺术家的形象,突然觉得他们很像在苍山中遇见的某些民间艺人。那些古老的艺术家画下了天堂与地狱的影子,他们同时也简化了天堂与地狱。我看到了一种穿过时间的粗粝画笔与粗粝的思想,以及对于世界尽头的粗粝想象。岩画的存在,在我们眼里变得虚幻和神秘。那些岩画背后的艺术家是虚的,是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可能被我们讲得有血有肉的。但很遗憾,在面对着那些岩画以及背后巨大的想象空间时,我们的讲述如此乏力,艺术家变得越来越虚幻。狩猎、放牧、采摘野果与舞蹈;人物、动物与植物。我们能看清楚的只是这些。内容似乎简单到轻易就能归纳出来。我们会有疑问,艺术能否被归纳?艺术的简化形态,艺术的小溪,那是某些艺术的源头。我们无法看清的颜料,应该是动物血液与赤铁矿粉的混合物。颜料是经过了怎样的糅合,才会有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消除走样的效果。这同样是个谜。
苍山中,有着一些无名的岩画与壁画。“在苍山中”——这是让我着迷的描述方式,我多次与人说起自己在苍山中。我还迷恋另外一种讲述方式——“我从苍山中来”。我从苍山中出来。我们在苍山下相遇。我们谈论到了此刻所在之地,有着众多的虫蚁,每到雨天,蛇就会出现,还有其他一些生命会出现。蛇出现了,别的一些生命出现了,它们从苍山中出来。岩画上有蛇,还有着其他的生命。对于那些岩画,我兴致盎然,我喋喋不休,那真是一些会让人产生无尽想象的岩画。我所迷恋的是岩画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不经意性,是一种随意的、有着童话意味的东西。
画师在那个庙宇里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于艺术的理想表达,画下了那些已经斑驳却依然华丽的壁画,基本都是一些神像。那个庙宇里没有人,我在庙宇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在那个空间里找寻着进入那些画的路径。画师离开那个庙宇,出现在苍山下的一些石头房子里,画着其他的一些画,从墙体上回到纸上的画。
在苍山中,会感知到一些衰败,也会在那些衰败中发现一些重生。我同样喜欢那些衰败,就像那个满是石头房子的村落,还有那个几乎已经被杂草覆盖的村落,没有人,超乎想象的人的缺失,但我依然喜欢那样的破败。石头房屋,就像是他艺术的牢笼,坚硬的空间之内,放置的是不是柔软和灼热的心?冰冷的建筑之内,特别是冬日,特别是雪下到了这个村落里,搁置的是不是一颗冷静的心?在面对着画师笔下的世界,坚硬、冷静的同时,还有灼热与柔和,石头房子显得很简单,而屋内的人与灵魂却并不如此,那是复杂的个体,是画师记录下的苍山上自然变化时,他自己内心的惊叹之声。我也想像那个画师一样,像那些梦想者一样,记录下自己每次进入苍山之内,会产生的一些惊叹之声。画师也可能在那样破败却杂草丛生(生命的两种极端:逝去与重生)中,开始画那幅在时间的沙漏里璀璨夺目的画卷。画卷记录了一种辉煌的过去,同样也是在记录着一种消失。
我继续以我的想象塑造着一个可能或不可能存在的画师。画师画完那些壁画后,来到了苍山下的那些石头房子里。画师不断画着自然,不断临摹着自然,让自己拥有一颗自然的灵魂。画师的那些传世作品中,自然的痕迹并不明显,而都是人,他展示着人在面对着名利牵绊时的诸多姿态。画师看得很清楚,他只有在苍山中才会看得那么清楚,才能真正做到超脱。一群人出现,一幅画又一幅画连缀在一起,时间有延续性,但一些神色却是停滞的,是重复着的。画师的行为近乎怪异。当人们跟我说起那是一个怪异的画师时,我理解了他的怪异,同时我又觉得那根本就不怪异。我想到了老祖的丈夫,那个在自然世界中抄写贝叶经的人,这个画师与他相近,他们有一些方面太像了。画师花了很长的时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苍山,真正的苍山之中,即便画师生活的世界背靠苍山,推窗就是苍山,他在苍山中临摹自然的同时,把那些临摹的草稿付之一炬(有点类似一些老人在焚烧那些甲马纸),将灰烬倒入了苍山十八溪中的某条溪流里(这同样类似那些老人把焚烧后的甲马纸的灰烬倒入其中一条溪流中),画师传世的只是一些人物画(那些人物画,我们能一眼就看到他们内心深处住着自然的影子,凝神细视,那是一些长得像树木的人,像河流的人,像天上云朵的人)。画师的一些作品,像极了夏加尔的画作,一些飞翔与梦幻的东西很像,羊群开始飞翔起来,那时羊群上是一些飞鸟,还有一些岩石也开始飞翔起来,还有人也开始飞翔起来。一些人进入了画师留下的日记之中,那些日记更多的是记录他每天在苍山中行走时所观察到的自然,在自然中嗅到的气息和所看到的一些在山崖上停驻的老鹰,以及在山崖间长出来的一些花朵。他详细记录下自己在苍山中内心的日渐宁静,还记录下他付之一炬的那些画。他详细记录着自己在那些真实的自然中,内心所发生的一些变化,那是自然对于生命的影响。只是日记中的几本毁于一场火,那些生命的文字如一些生命般灰飞烟灭,让人唏嘘。画师还留下了一些混沌强烈的画,他画下的是对于苍山的一种无能为力,努力却看不懂的苍山,越熟悉之后越看不懂的世界。内心的罗盘,早已辨不清方向。在惊叹之中,覆盖在苍山上的雪与天上的飞鸟,冻结了罗盘的感应能力。画师画下了沉默的罗盘与寂静。画师画下了一种独属于自己的复杂性,那是作为个体不应该被剥夺的复杂性。
那同样也是一幅长卷,至少五十多米,画卷被缓缓展开;时间是现在,画师是一个女的,她所记录的同样是一种逝去与重生。那些石头的世界,松果般的形状与纹路,生命的尽头进入了那些石头。石头是坚硬的,但最后的那块石头已经破碎,一些东西碎落了,那时一些隐喻的东西出现。你无法去评判那幅画卷。你同样无法说那就是一种模仿。眼前的画师,说她一直在构思着这幅长卷,有很多个夜晚,她无法沉睡,往往一有想法就会点灯披衣。她说自己就像是被那个几百年前的画师附身,画下人在自然中的那部分,当年的画师并没有完整画下人在自然中的样子。她画了太多的石头。如果我跟她说苍山下有这样一个村落,村落里有着众多的石头房子,像极了她笔下的那些石头,不知道她会有着什么样的反应。你似乎看到了对一个影子的虚幻模仿,一种想对影子的努力捕捉。你一眼就发现了两个艺术家所要抵达的艺术的维度是不一样的。你不好随意评判眼前的那个画师的画卷总有种对于宏大的迷恋,至少是对于长卷的迷恋。她再次强调了那幅画卷有着五十多米。画卷没有完整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它只是一部分一部分被展示,某些部分永远是被隐藏着的。
黑色笔记本之一
在苍山中的那个村落里,所有的灯火早早就熄灭了,人们早已躺到床上,大家都在静静等待着亡灵的回来。苍山中的那条河流在厚厚的夜幕中,响声清越,还有点点冰冷,落入河中的星辰也感觉到了那种透心的刺骨。
白天,在苍山中的那个村落里,一场丧事刚刚办完,一些人沉浸于悲痛中还未能缓过来。暗夜里,夜是忧伤的,忧伤的心亦无法真正入睡。在人们的讲述中,亡灵会踏着冰冷的月光回来,月光很淡,只有亡灵才能看清淡淡的月光照出来的路。人们把亡灵生前最重要的物件摆放在了坟墓前面:一根拐杖、一个烟斗……
夜晚倏然而逝。人们都说那个夜里,亡灵是回来了,人们听到了他在门口抽了几口烟,磕了几下烟斗,就进来了。亡灵要轻轻碰触一下亲人,但亲人不能动,一动就会吓着亡灵。虽在世之时是无比亲切之人,但面对着亡灵,很多人依然感到害怕,只能忍着,只能屏住呼吸,许多人在恐惧中慢慢沉睡。亡灵忘记了烟斗。人们还看到了磕烟斗时留在门口的灰。那都是亡灵回来的痕迹。亡灵的亲人,把烟斗展现给大家,就为了证实亡灵曾经回来过。
人们说,在尸骨被安葬的那晚,所有的亡灵都会回来,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冰冻湿滑,那时那些年老逝去的亡灵,有了重返青春的力气,他们留在夜间的脚印,与常人无异。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人们说起一些年老的亡灵时,都肯定地说他们听到了亡灵走路时喘气的声音,还信誓旦旦地说起看到了亡灵停步歇歇气时,令人悲伤和怜惜的身影。
我参加了其中一次葬礼,那一晚,我猛喝了几杯酒,早早就躺了下来,冰冷与恐惧让我很长时间不能入睡。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入睡,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是翌日,人们开始纷纷说起亡灵回来的事情,所有人都面露肯定和激动的神色。我也丝毫没有怀疑,毕竟在我的记忆中,在人们多次说起之后,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即便在众人的异口同声中,一些可疑的东西依然呈现在人们面前。即便时间继续往前,人们对于亡灵的认识依然是这样,至少在苍山下的那些村落里是这样。我离开了那个村落,人们依然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亡灵回来的情景,这次亡灵忘在家里的是拐杖,那根支撑着生命度过了众多严寒冬日的拐杖。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了那根被时间擦亮的拐杖。信与不信,有时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离开了那个村落。白日,河流的声响在人们喧闹的讲述中变得小了很多。我远离了人群,我沿着河流走了很长的路,才真正从那个村落里走了出来。在与那些喧闹的人群有了一些距离后,河流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河流变得真实起来,我俯下身子,像牛饮水一样长长地喝了一口冰凉刺骨的河水。
二
苍山中至少有三百多种神灵。岩画中画下了其中几种。岩画所在的那个石崖,也被人们当成是神灵的一种,石崖下面留下祭祀活动的痕迹。他说到了具体的数字,在说出“384”这个数字后,他又说不只是“384”。他在苍山中说到了这个数字。数字的出现,成了一种强调,似乎是在强调数字的一种落寞。现在,人们所认为的出现在苍山中的神灵的数量早已没有这样多了。几百种神灵,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神灵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很庞大很丰富的、对世界认识的不一样或者是对世界认识的趋同。那是人们在苍山中生活时的一种状态,神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交叠。每个人的心中,至少活着一个源自自然的神灵。真实的是神灵不只是自然中的生命,神灵还可以有其他的种类。在我不断进入苍山后,我同样与神灵的多种形态相遇,也在这样多种形态面前感到惊诧,感到有一种近乎幻梦般的对于世界的认识,那是属于苍山的对于世界与自然的认识。与这么多神灵相遇,也是在与一些稀缺的精神重新相遇。似乎我又开始陷入大词与虚夸的世界之内。但真如自己在与一些人说起的那样,我只希望自己的某些方面能够得到重新塑造,那种对于思想卑琐的抗拒,那种对于清洁精神的渴求。
他提到了桤木树中的柴虫,那也是神灵的一种。这时我们脑海里开始出现一条白色的虫子,在树木中空的部分慢慢爬动着,用赤与黑交杂的唇触摸着树木的内部,似乎舔舐一下,树木就会颤抖一下,然后不断往空里退。我们脑海中还出现了有着众多桤木树的村子,那是苍山中的村子。我们先是在苍山中的另外一个角落看到了一棵桤木树,很粗壮,仅此一棵,那时我已经觉得依然存在那样一棵树已经是不可思议。没想到在这个村落里,有着大量的桤木树。眼前的桤木树粗壮繁盛又奇形怪状。一些桤木树已经死亡,上面长出了丰茂的其他寄生植物。我们听着自然的声音。好久没这样把自己放入自然了,鸟鸣,风的声音,树木的声音,很少的人声。那些古木中将有着多少的柴虫,那里将有着多少的神灵?我第一次听说了柴虫同样也是神灵之一。他还提到了蝴蝶。他还提到了岩石(在提到岩石时,我想起我们村所信奉的神灵便是岩石,我们村子背后就是赤岩堆起来的山,进入我们的本土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简化为木牌的“赤岩天子”),心中如岩石一般,有的如岩石一般的精神。他还提到了古井,提到了其他。那时神灵幻化为一只柴虫在巨大的桤木树中活着,被桤木树滋养着。桤木树下蓝色的阴影里出现了一只柴虫,它探出了头,又在我们的目睹下慢悠悠地把头缩回古木中。我在周城,看到了作为塑像的大黑天神,而在这之前,大黑天神就在我们村的庙宇里,以一块木牌的形式存在着,他们是同一种神灵,只是存在的形式不一样。
在苍山中,神灵系统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进入那些本主庙中,举行一些为了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指向、五谷更好地生长、牲畜健康,等等的祭祀仪式。
离开那个有着许多桤木树的村子,也离开了某个正在举行的祭祀活动,我出现在苍山下的另外一个村寨里。我喜欢进入苍山中的那些村寨,拜访一些老人。这样的拜访很重要。有时我甚至会有一些偏见,那些老人心中存留着不一样的、已经不可能在此刻能看到的苍山。在高黎贡山中生活的那几年,我有意去山下的那些村落里拜访一些老人。我认识了老祖,认识了老祖口中的丈夫,还认识了那个民间的歌者。在苍山中,同样有着这样的老人。
当我在苍山下的周城时,遭到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群老人。一些安静地做着扎染的老人,她们的服饰上铺满如蓝天般的靛青色,靛青色的围腰、头巾、衣服,她们低头凝视并不断穿针引线。她们在缝制一些图案,似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一种努力,要完成对于那些蓝色中纯净的白色图案的理解。那些图案在扎成一团成皴的布里,打开,晒干,你看到了最终的图案,其中有些图案就被那些老人穿在身上。那是你在回想着成皴的布时,不曾想到的。其中一个老人正在安静地制作扎染,她正在制作一只蝴蝶。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图案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图案的艺术化,以及艺术对我们的浸染上。
黑色笔记本之二
当铜壶被挖掘出来时,她并没有感到诧异,她以为这次挖掘出来的依然是以前常见的那种铜壶。当那个负责修复文物的老人把上面的泥土和尘埃慢慢地刮擦干净之后,铜壶变得不再那么寻常。在苍山下这几年的挖掘考古发现中,那个铜壶是如此独一无二。这个铜壶上有着羽人的图案。别的铜壶上都没有羽人。作为考古者的她,在苍山下第一次遇见这样飞翔起来的物件。铜壶有种要羽化的感觉。飞翔被时间的尘土一层一层地覆盖。她觉得如果自己没有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尘埃拭去的话,它总有一天真会消失。她说自己成了一个梦想者。她成为考古者中的一个,就是想把苍山中那些被掩藏着的东西挖掘出来,她对那些美的东西,那些可以打开无限想象空间的东西很痴迷。我出现在她所说的那个村落,一切都很平静,一切都已经或正在消失。考古的现场已经消失,就像考古的人不曾来过一样。也许某天他们还会回来。他们离开后,那些现场被填了起来,在草木繁盛之际出现的,只有那些不断生长的草木。
她想轻轻地抚触着那个铜壶,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那个翅膀被她接触后可能就会折断。翅膀从铜壶上折断,掉落在地,在空气中将彻底消失。铜壶需要经过专业的处理。那时她在几重身份间转换,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部装着好几个自己,那些自己都想把考古者的身份掩盖,内部那个作为纯粹审美者的她最终占了上风。她成了一个纯粹的审美者。
那时,铜壶羽人出现在博物馆里,躲在暗处,但她一眼就发现它所在的位置,这与她在苍山下考古时一开始的茫然无措不同,那时她更多是靠运气,她无法肯定一层又一层的土下面会有什么。铜壶羽人出现了。她以为自己会遇到更多,她感到一阵窃喜,不断深挖,不断把范围扩大,但就仅此一个铜壶,也仅此一个羽人。她慢慢平静下来,一个已经足够。她又回归到了纯粹的审美者状态,那种穿越了许多时间,依然释发出斑斓灿烂的羽翼,已经让她不再贪婪。她在苍山下的那个村落里,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她带着那个已经经过专业处理的铜壶羽人,离开了村落。落日从苍山上落了下去,天色渐暗,一股冷气袭来,羽人已经被放入博物馆。此刻,落日将尽,我还舍不得离开苍山下的那个村落,我也在想象着那些色调单一的土层之下掩埋着类似羽人的东西,那里可能还掩埋着会让想象飞升的翅膀。
三
在这之前,我们在苍山西坡的村寨里,见到的都是一群人在打歌,众人参与。打歌往往发生在夜间,在篝火旁,喧闹的世界,人们在那样的情景下尽情释放着自己,尽情享受着快乐。当我们融入那些喧闹后,又隐隐感觉到自己只是暂时忘却了世界中充斥着的分歧与苦难,我们知道至少那些属于个人同时又是群体的苦难一直还在。似乎只有众人簇拥在一起,内心深处的那种无尽的孤独感才会有所稀释。在苍山西坡,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群体喧闹的方式。打歌是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打歌在苍山中的一场婚礼后进行,那时获得的就是快乐;打歌还在一场葬礼前进行,那时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纾解内心的愁苦。我不曾想过,在苍山中,还会遇到与我们的习惯完全相悖的打歌,只有一个人的打歌。
我们在去往雪山河的路上,他们跟我说起了那一个人打歌的村寨。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这样的世界开始很向往,毕竟这是与我的常识不一样的世界。在苍山西坡,一个人在那里跳舞,有独舞的意味。这种打歌出现在那个村寨,现实的一种。有人就在我们前面打跳,用彝族语言唱着些什么。因为这种语言与我熟悉的白族话不同,在听的过程中,竟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里,那只能是语言的陌生所可能抵达的陌生,并有一种奇妙的误读。那时,我不用去关心语言。其实,我又怎么能轻易忽略那些语言呢?即便说的都是白族话,但在苍山中,因为小的山河村落的切割,就让它们有了一些细微或明显的差别。语言背后,我们遇见了一些独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甲马、对歌、鬼街(鬼与世人的节日,更多是鬼的影子,许多人说在那个近乎狂欢的节日里,你会碰到很多已经逝去的人,一些人带着对逝去亲人的无比思念,在那个特殊日子里,出现在苍山下的那条街上)……
一个人的打歌,也是祭祀仪式的一种。不知道那是祭祀时的舞蹈之前,我们觉得那是沉醉于近乎虚幻中从而摆脱孤独的舞蹈,是极简主义的舞蹈。这也是我们在面对着那种舞蹈时,最为合理的解释。有些时候,在苍山中,很多的东西都变得不再那么合理。那些不合理的东西,不断冲击着你的内心,让你的内心在面对着那种情境之时,会对世界产生新的认识。同时,在各种解读面前,它又马上以悖论的方式出现,让人不知所措。在苍山中,我慢慢放弃了那些放任的臆测。
在苍山中,那种看似孤独的舞蹈,其实并不孤独。那个跳舞的人说,我是在与苍山中的那些树木共舞,你们看到那些树木在舞蹈吗?我望向了树木,树木静止不动。那是给自然之神跳动的舞蹈,一些人这样说。那时,现实与我们所希望的似乎完成了平衡。在苍山西坡的火塘边,眼看火焰渐渐暗下去,我们开始感觉到了睡意,有人却不希望我们睡去,他到外面的星空下向星星借了一抱柴火,房间再次亮了起来。我们看到了有个跳舞的影子,舞者的真实身影却看不见。那时,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到了那样的情景,我也不敢跟人说起自己看到了一个跳舞的影子。当我还在犹疑时,有人把我拉了起来,我们一起跳舞,跳起白日里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人的舞蹈。它成了一种群体的舞蹈。当自己也能成为舞蹈的一部分后,再也感觉不到那是一种呈现孤独的舞蹈。世界,给人呈现出了另外一面。
苍山西坡的这一晚,我们所感受到的便是世界的多重维度。在众人尽情舞蹈时,特别是在其中一夜,打歌在夜空之下进行,那夜繁星璀璨,我们忘却了在苍山中还有一些属于孤独与忧伤的舞蹈。那夜,我说不清楚是否有着一些孤独的影子也混入了我们中间。那一夜,有着各种思绪复杂的人,同样有着各种单纯的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火塘,又是不一样的火塘,身处同一个夜空,又是不一样的夜空。那一夜,我并没有梦到自己在苍山中,孤独地跳起了那种简单的舞蹈。在一座城中,孤独感越发浓烈之时,我竟然梦见了自己在苍山西坡的一个陌生的村落里,笨拙地跳着那种舞蹈,一步,两步,到七步结束,接着重复,然后开始慢慢有了变化。我猛然意识到岩画中有着那些舞蹈的影子。
黑色笔记本之三
人们聚集在庙宇里。庙宇往往是苍山中每个村落自己的本主庙。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为了寻找那些走失的魂。那些因魂走失而变得体弱多病之人,那些因魂缺失而萎靡不振之人,还有那些受到惊吓的孩子,他们纷纷来到了那里。等所有的祭祀活动结束,把鸡头、鸡骨头、鸡尾巴上面所暗示的一切信息慢慢看完之后,那些魂走失了的人都留了下来。
我看到有很多人留了下来,这也意味着许多人活在了失魂落魄之中。大家都需要把曾经的自己重新找回来,能否顺利,就看祭师能否帮自己找到,或者是在祭师的暗示下,自己能否在那些角落里找到。那种行为,似乎也在暗示着要想找回真正的自己,靠祭师的同时,还要靠自己。祭师拿着点燃的香进入庙宇之内,他们也跟着祭师进入其中。有一次,我也跟着祭师进入了庙宇。那时年少的我被一窝马蜂蛰了,昏睡了几天,等苏醒过来后,变得颓靡不振。不用让祭师掐指卜卦,父亲就肯定地说我的魂弄丢了,同样需要去庙宇里把它找回来。祭师口中念念有词,念得很轻,很少有人能捕捉到祭师口中的只言片语,大家都不会感到遗憾,一些人还感到庆幸,毕竟那些语言,还有那种表达虽与自己有关,交流的对象却不是自己。在我小的时候,曾多次认真听过祭师的话语,只能捕捉到一些人名和地名,那是具体所指的东西,别的我没有听清过。随着年龄渐长,对世界的感觉退化变弱之后,要听清祭师的话语就更是不可能了。
祭师用香熏着那些角落,里面有着一些蜘蛛网的地方,那是魂依附的虫子生活的地方。那是像蜘蛛一样的虫子。我们都相信丢失的魂已经幻化为那种虫子。有时它们很快被我们找到,有时没能找到它们,我们的喜笑颜开与颓丧失落都写在了脸上。没有找到的话,还将至少举行一次祭祀活动。找到的虫子,被放入炒熟炸成米花样的苦荞中,封存起来,放到家中的祭台上。苦荞炸裂开来时,我们用锅盖盖着,但苦荞依然掉得满屋子都是。为何我们的魂就只是那种虫子,为何就不能是其他的虫子,像竹节虫,像蝗虫,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像豹子,像老虎?我们细细思量后,一致觉得很容易就被忽略、生活得也很卑微的虫子是魂的合理。在苍山中,我又遇见了一些人,他们同样在找寻着丢失的魂,他们说要找回那种向死而生的力,还要找回健康而熟悉的自己。
李达伟,作家,现居云南大理。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暗世界》《大河》等。
《天涯》2023年第2期 目录
作家立场
004 林渊液 大象:中医采访与思考札记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020 唐克扬 梦境和历史的风景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026 赵大河 九歌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小说
037 韩松落 写给雷米杨的情歌
056 蒋一谈 空钵
062 吴昕孺 父子长谈
“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
080 羽瞳 线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095 章程 正午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05 王晓雯 远山(外一篇)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19 罗志远 夜行家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29 孟祥鹏 去瑶池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38 李晨玮 燃烧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48 巫宏振 日记簿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散文
“边地的风物”散文小辑
156 裴海霞 荒野牧人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62 刘予儿 风中的石头房子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71 刘梅花 白石篱笆 (点击标题跳转阅读)
180 李达伟 岩画
186 千忽兰 命运里的符号
艺术
193 唐棣 巴黎不属于任何人——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之六
环球笔记
206 爱迪生的混凝土住房梦/“全球南方”与城市研究/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人/黑死病与欧洲的崛起
点击封面,一键购买
戳 “阅读原文”一键购买本期《天涯》!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