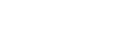编者按
“文学观澜”是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专刊,其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版旨在总结获奖作品以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我们邀请作家、评论家或回顾重温获奖者的代表作品,或把脉其创作整体风格,或解析其近年文学创作,力图形成多元立体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新貌。
作家介绍
李佩甫(1953~),河南许昌人。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李氏家族》,出版有中篇小说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钢婚》《田园》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长篇小说《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生命册》作者:李佩甫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出版日期: 2021-4
李佩甫心中有个“好的故事”
孔会侠
1925年1月28日,是个“昏沉的夜”,鲁迅先生“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学记》”,沉入一场轻松美好的梦境。那里“美丽,优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如果我们和《社戏》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梦境其实是他童年记忆的提纯和再现,那时,他在平桥村外婆家的生活对少年鲁迅而言,“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往事念念不忘,就有了这篇平和优美的散文诗《好的故事》。
李佩甫心中也有个“好的故事”,事发中原,与鲁迅先生状况类似。
1986年,李佩甫在《莽原》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红蚂蚱 绿蚂蚱》,深情回忆了他在蒋马村姥姥家的童年生活。在那里,他是跟在表姐屁股后面的“小脏孩儿”,在苍绿的田野间自在游荡,“捧着乡下孩子的小木碗,我就这样一家一家地吃遍全村。吃了,和小小的‘老表们’滚在土窝里脱土馍馍,木碗儿扣出光光圆圆的一坨、两坨、三坨……撒一泡热尿,那‘馍馍’碎了,又脱。”
乡村的童年生活于他们,是一场命运恩赐,成全了他们对整体中国的实感经验,也积淀下在光阴中不断发酵的温暖情感。这情感,不仅长久慰藉着他们成人后的精神痛苦,还将成为他们文字世界的来处,由这情感决定的思想方向,也将成为他们文字世界的去处。
1983年,刚刚调到《莽原》杂志社任编辑的李佩甫经历了两件对他影响深远的小事:一是在办理调动手续时,他亲历了别人一天盖好几个章自己却一个都没盖成的困窘无助;另一件是他去单位电工房借一把钳子,谁知电工师傅“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赔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也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吗?我扭头就走,到商店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
这是典型的“底层经验”。在人际关系的铁网面前,李佩甫和许多来自乡村、渴望实现生命价值的青年们一样,领教了人情世故真实而严酷的一面,他们感到愤怒,内心疼痛,他们生出了不甘不服、发狠努力的斗志。是的,“不为钳子,为尊严”。
现实遭遇总能将少时单纯美好的生活记忆撕出裂缝,无法弥合。在这裂缝中体验到的、思考到的,构成了李佩甫作品的情绪和价值。
此时,李佩甫的写作已在迷茫中摸索了5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向和风格。但冥冥中,童年记忆牵出的乡村情感和初来郑州的“底层经验”正在互融,并在《古里雅的道路》(小学三年级阅读过的)和少年时社会激情(集市上协助公安抓小偷)的催化下,于1980年代“启蒙”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他社会理想的基本构型,虽难以具体描绘,但有几个核心特征:社会运行公正、平等、仁爱、有序,人们衣食无忧,活得独立、健康,有尊严,愿奉献。这成为他观察生活、审视生活、批评生活时参照的标尺。
据此,他终生写作的主题走向暗自初成。
1984年,李佩甫在《奔流》第5期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森林》,他“想描摹出三条有血性的硬汉子”,是如何含辛忍辱开垦荒山,希望创造出可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的事业来。在这篇小说中,他开始将青年农民的努力奋斗作为表现现实的主线,他开始发出追问:在辛苦的谋生路上,中原农民在庞大而有等级的社会体系中如何存在,如何获得尊严?为什么如此?在延此方向的理解和思考越来越成熟后,他将之总结为“土壤/植物”关系学(即“人与土地”关系学),其实就是,卑微如草的农民是怎样一步步被环境塑造成或低伏、或变形、或不屈的生命形态的。“土壤/植物”关系最典型有力的说明者就是内具了和李佩甫一样性格特征的奋斗者们,这个家族成员众多,有男有女,有时是小说聚焦的主角,有时是几笔带过的配角。《森林》中这三位面目模糊、蕴蓄能量积极打拼的乡下青年塑像是这类人物的首次亮相,然后是《小小吉兆村》中的山根,《金屋》中的杨如意,《豌豆偷树》中的王小丢,《败节草》中的李金魁,《城的灯》中的冯家昌……直到《生命册》中的吴志鹏。
李佩甫将自己的眼睛附在了这类人物身上。因此,小说中,他们的人生经历相对完整:小时候在农村人群场受尽歧视,养出了满目攒动的“黑蚂蚁”;进城后施展各种手段打通关节,追求权力和金钱的逐步拥有,后来终于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跟随着他们,李佩甫的小说形成了“两地书”的结构。在“乡村/城市”的生活场景转换中,李佩甫不仅观察到了权力支配下仁义与薄情混合的农村人情关系,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还观察到了城市这个名利场盛行着什么样的生存规则,演化着什么样的时代风习,人们是如何渐渐蜕变的。
当然,作为叙述者的李佩甫与他们不尽相同,但他能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过去/现在”“乡村情感/城市生存”“回归/离开”等之间的纠结、矛盾、迷茫、困惑、痛苦、寻找,李佩甫也能感同身受。因此,他们强烈丰富的精神体验反哺出李佩甫作品的思想意蕴。
在李佩甫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生命册》是耗费心力最多、写作时间持续最长的,历经5年,他将50多年的生活经验和30多年的写作经验重新盘点,再次反刍,努力克服了以前写作上的峻急不耐,扬长避短,实现了叙述状态和立意上的双重突破。尽管,很多人认为《羊的门》是李佩甫最好的作品,切入了中国式生存的根部,寓言性强,涵义深厚苍凉。《生命册》中,被诟病的“半部现象”不见了,他的情绪日渐缓和,面对社会世相更加理性宽容,叙述语言一以贯之平和从容。而且,在最后一章做集中表意时,他的思想在“水尽鱼飞”和寻找“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两处得以升华,超越了以前作品多在现实层面总结追溯,频陷于矛盾纠结的局限,有了些辽远、沉静、空灵之感。
《生命册》的主人公吴志鹏,像是李佩甫个人形象的“孪生”,他距离李佩甫的经验、情感和思想最为切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背景”就是李佩甫的“背景”,他“背着土地行走”的不堪负重就是李佩甫的不堪负重,他身处时代旋涡时的清醒抽离和旁观就是李佩甫保持距离的警觉,他对故乡的陌生和回不去的慨叹就是李佩甫的陌生和慨叹,他涉入时代生活旋涡的内审和认知就是李佩甫的内审和认知,他于茫然中立志寻找理想社会形态的固执就是李佩甫顽固多年的情结。李佩甫很看重这个人物形象,“在他身上下了最大功夫”,也寄予了希望,他“大体上是一个清醒的人,通过不断地内省,他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人的”。以他的经历为线索,《生命册》连贯起了对中国社会乡村与城市、过去与现在的整体展示,还有对未来的遥望与期待。
李佩甫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他的视角里”了。
在《生命册》的最后一章中,吴志鹏在阔别故乡三十多年后,再次站到了那片土地上,他举目四望,处处陌生,记忆中的乡村物事和场景已经消逝于时光中,擦肩而过的是一张张不曾相识的面孔,耳边响起的乡音没有变化,但那说话的内容和语气却已经是商业思维下的吹嘘欺骗……返回熟悉的故土却发现这思乡之情无以归依,吴志鹏沉浸入对另一个时空的留恋中,他的内心放电影一般,将往事中的乡村情景细致地一一予以特写:“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瓦沿儿上的滴水”“夜半的狗咬声”“蛐蛐的叫声”“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倒沫的老牛”“冬日里失落在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简易的、有着四条木腿的小凳”……这个片段李佩甫很喜欢,不仅单独成章地刊登,还专门收录进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北中原的情书》中。
这是他心中“好的故事”,再次重温,成了怀乡情感的唯一寄托。
故乡已物是人非,村上的木材加工厂肆意喧嚣,树木被滥砍滥伐,农村的自然生态在追求物质化进程中遭到了触目惊心的破坏。他这样写道:“在咱们的家乡无梁,原本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芦苇绵延百里,一眼望不到边,好像一生一世也割不完、走不出的样子。苇荡的尽头,有一个大水潭,名为:望月潭。民间也有叫‘老鳖盖’的。据老辈人说,这潭有几百年了,从来都没有干过。……可是,三十年过去了,整个芦苇荡都消失了,望月潭也干了。可那锅盖大的老鳖呢?鱼们呢?没有翅膀的鱼,飞到哪里去了?”在此处,李佩甫提出了“水尽鱼飞”的生态关系命题——依存,万物(老鳖、鱼、人类)是要在大自然提供的条件下生存的,如果这条件没了,仰赖于此的物种也就没了。按这顺理成章、合乎自然之道的因果关系来推,人类的生存基础是什么?人类该如何才能持续在地球上繁衍下去?在这个点上,李佩甫作品的立意实现了第一个升华。
结尾处,吴志鹏接连两次表达心志,语气真诚坚定:“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儿子或是孙子去找。”困惑和追问,忧患和批判,是李佩甫过去文本的主音,这次,他仍然立足现实,仍然有感慨和不解,但他更愿意去探索,寻求一种能让家园美好、和谐、重焕生机的良方,他愿意付出心血,他相信未来有实现的可能。
2011年3月,中国作协七届十一次主席团会在北京召开,李佩甫当时做了《文学的标尺——时代与文学的断想》的发言,呼吁文学要重视国人的精神,要积极发挥济世立人的建设作用。他说:“我们知道文学对具象的社会现实没有实际的效用,可我们更知道文学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先导,文学是人类精神之药,可以滋润人的心灵的。真正的文学语言应是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文学对社会、人心的建设作用,是李佩甫近些年多次强调的。
《文学的标尺》和《生命册》是李佩甫的回向,给热爱几十年的故乡,给热爱几十年的文学。
写作者心中有个“好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呢?写作者心中没有“好的故事”,又会如何呢?
相关阅读:
茅奖系列之王蒙 | 共和国文学之子
茅奖系列之王蒙 | 作为方法的意识流
茅奖系列之刘玉民 | 中篇小说的困境与突围
茅奖系列之刘玉民 | 史诗与史识
茅奖系列之格非 | “讲故事”:回溯与开拓
茅奖系列之格非 | 尚待命名的小说写作实验
茅奖系列之刘震云 | 先锋姿态、批判精神、创新追求
茅奖系列之刘震云 | 一次出走,或一万次精神自赎
茅奖系列之毕飞宇 | 毕飞宇的目光
茅奖系列之毕飞宇 | 从历史主体到情感主体
茅奖系列之莫 言 | 认同危机·拓展故乡·拷问灵魂
茅奖系列之莫 言 | 《晚熟的人》读札:记忆的在场或声音的荒原
茅奖系列之刘醒龙 | 《天行者》:塑造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
茅奖系列之刘醒龙 | 关于刘醒龙的四个思考片段
茅奖系列之张 炜 | 赓续雅文学传统,重筑审美乌托邦
茅奖系列之麦 家 | “讲故事的人”
茅奖系列之周大新 | 周大新小说的文化阐释——由《湖光山色》说开去
茅奖系列之迟子建 | 关于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以有情的方式构建美
茅奖系列之贾平凹 | 重读《秦腔》:古镜未磨,照破天地
茅奖系列之宗 璞 | 《野葫芦引》: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茅奖系列之柳建伟 | 朱向前:柳建伟和他的“时代三部曲”
茅奖系列之徐贵祥 | 新作《英雄山》:英雄传奇的“现代性”重构
茅奖系列之熊召政 | 刘复生:历史小说的转折与《张居正》
茅奖系列之王旭烽 | 曾镇南论《茶人三部曲》:茶烟血痕写春秋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题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12月22日第5版
编辑:刘雅
二审:王杨
三审:陈涛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