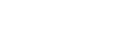杨公骥简介
杨公骥(1921.1.16-1989.6.7)河北正定人。著名社会科学家,文学史家。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名誉主席,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职。论著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文艺、语言、训诂、考古、民俗等学科,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杨公骥基本资料
中文名:杨公骥
别名:杨正午,杨振华,杨公忌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北正定
出生日期:1921年1月16日
逝世日期:1989年6月7日
职业: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毕业院校:武昌中华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
代表作品:《中国文学》(第一分册)
指导的博士生:李炳海,赵敏俐,许志刚等
性别:男
杨公骥生平简介
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开始编写于1948年。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另创格局。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承认、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同样角度,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此为杨公骥先生195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论文。“巾舞”又名“公莫舞”,原是汉代的歌舞古辞,共308字。但由于“声、辞杂写”,自“江左以来”已“讹异不可解”,换言之,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已无人通晓。经杨先生逐字逐句地反复考辨,分别词类加以句读,于是巾舞歌辞的本辞、复唱、叹词、和声与标示角色、舞法、舞步、手势的字句便由混缀成一片的文字中分离出来,从而呈现出汉时巾舞的原貌:是表演“母子离别”情景的。1985年,杨先生对旧文作了增订,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的题目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公莫舞》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破译的最早的歌舞剧,因此在文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界,被广泛重视。
此书出版于1962年。所谓“唐代民歌”是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从《敦煌缀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的,共选二十八篇。杨先生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索出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如果根据内容考证年代,则最早的民歌作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至九年(621-626年),有些篇作于太宗、高宗、武后时代,最晚是作于玄宗天宝中期(750年前后)。时间跨度约为130年,显然非出一手。这些民歌(今查出托名王梵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关于“变文”,经多方考证,杨先生认为“变”("变相")乃是寺院的壁画或画卷,所谓“变文”就是图文,乃是解说“变”(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韵文)合组文体的承袭。杨先生除引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所谓“变”(图画)和“变文”(图文)乃是继承我国古代“图、传、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题韵文的“诗”,这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在1978年发表的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干》(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2期)中,杨先生运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依靠文字解说语言,不根据字形考据字义,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也就是将语言现象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心理反射、思维活动、认识过程相联系地进行全盘思考与综合研究。这样便可由语言现象的偶然性中发现语言规律的必然性。可贵的是,所有这些不是作空泛的理论性论述,而是根据“桢”、“干”等许多古语词(概念)的引申变化过程来作实证,以解释语言规律。姜亮夫先生曾写道:“最近读到杨公骥先生考证桢干一词的文章,以哲学的观点论证汉语语根的唯物的‘生’的基础与辩证的发展。用这样一个具体材料,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的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学习的文章。”
杨先生1980年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一文。文中,杨先生首先通过周详的考证,说明了《诗经》《周易》和许多古文献中所记述的古人居住的“陶复陶穴”(即“窟穴”、“穹室”、“环堵”)的结构样式:作圆形或方形,半在地表下,半在地表上,壁下部开门户,穹形顶上开有天井(古名“中霤”、“屋漏”)用以通气透光,严冬时可由此出入。这种半地下式的“陶复”地窟,不仅见于古书记载,而且直到19世纪末,仍是吉林、西伯利亚东北部某些民族住室的基本形式。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在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现了这种“陶复”式地窟的古代遗址和后世残存。在黄河流域河北磁山发现的陶复式地窟,经过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794年。由此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古代黄河流域人与东北亚(及阿拉斯加)人便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共同性。进而,杨先生从民族民俗学角度,对两个地区民族的神话祭礼仪式风俗作了精细比较和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如:“冬窟夏庐”、祭中霤、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祭拜月亮、五月祓除祭、逐疫鬼、送瘟神、赛船、挂五色长命缕、辟五毒、投祭物于水中、日月蚀时击盆、逐“天狗”、祭北斗星求长寿、“立尸以祭”(以活人代神或以萨满代神)、雷神执雷斧、祭龙、大傩、方相(萨满装束)、磔狗。这些传统习俗大同而小异,足以证明黄河流域与东北亚有着长期的密切的文化交往与联系。此文由于证据多、论断谨严、见解独到而受到重视。
1980年写就的《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连续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第1、2期。
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把周代视为“奴隶制时代”的权威说法,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根据是否“杀人殉葬”,是否“用人为祭牲”、“杀人祭祀”,是否把人“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是否“贩卖人口”、“人价低于马价”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他引述了马克思区分社会性质、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人身被占有,所以表面看来,奴隶的所有劳动,似乎都是“无偿劳动”,但实际是在“无偿劳动下掩盖着有偿劳动”,因为奴隶主为了使奴隶活下去从事再生产,就必须从奴隶的劳动“所得”中拨出一部分“偿还”给奴隶,作为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农奴从属于领主,在领主的田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三天(即“公田”劳动),再在“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三天”(即“私田”劳动),所以农奴“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作为“雇佣者”从事劳动,做一天给一天工资,“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但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剩余劳动构成了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天才的马克思极其明确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社会经济性质的区别,也为历史分期提出了标准,所以恩格斯说:“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杨公骥据此认为,只有根据剥削形式,也就是根据“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来进行历史阶段分期,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如依此论断,则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占有一小片土地”的,“成家立业”的有自己生产资料的,有“家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所谓“奴隶”,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农奴”。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涉到中国上古史分期的争论,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判断认识周代和先秦社会的性质问题,对先秦的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风俗史的评述等都有重大的影响。杨公骥有理有据的辩驳,是当时国内关于上古历史分期争论中很有分量的一家之言。但是要对郭沫若这样的权威进行挑战,即使论据再充分也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杨公骥先生的批判文章,常常是文字老道、辛辣,好像有些给人不留情面。挑战权威,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杨公骥先生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盲从流俗,不迷信权威,他总是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然后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每提出一个驳论性的观点,都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穷尽式地搜集资料,不只是搜集肯定自己观点的材料,更注意搜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通过客观的比对,然后才得出新的结论,所以他的文章总是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坚持追求学术真理,求实问是,敢为人先,这也是他多年来为学生所树立的榜样。
杨公骥生平轶事
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开始编写于1948年。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另创格局。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承认、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同样角度,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此为杨公骥先生195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论文。“巾舞”又名“公莫舞”,原是汉代的歌舞古辞,共308字。但由于“声、辞杂写”,自“江左以来”已“讹异不可解”,换言之,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已无人通晓。经杨先生逐字逐句地反复考辨,分别词类加以句读,于是巾舞歌辞的本辞、复唱、叹词、和声与标示角色、舞法、舞步、手势的字句便由混缀成一片的文字中分离出来,从而呈现出汉时巾舞的原貌:是表演“母子离别”情景的。1985年,杨先生对旧文作了增订,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的题目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公莫舞》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破译的最早的歌舞剧,因此在文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界,被广泛重视。
此书出版于1962年。所谓“唐代民歌”是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从《敦煌缀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的,共选二十八篇。杨先生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索出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如果根据内容考证年代,则最早的民歌作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至九年(621-626年),有些篇作于太宗、高宗、武后时代,最晚是作于玄宗天宝中期(750年前后)。时间跨度约为130年,显然非出一手。这些民歌(今查出托名王梵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关于“变文”,经多方考证,杨先生认为“变”("变相")乃是寺院的壁画或画卷,所谓“变文”就是图文,乃是解说“变”(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韵文)合组文体的承袭。杨先生除引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所谓“变”(图画)和“变文”(图文)乃是继承我国古代“图、传、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题韵文的“诗”,这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在1978年发表的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干》(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2期)中,杨先生运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依靠文字解说语言,不根据字形考据字义,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也就是将语言现象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心理反射、思维活动、认识过程相联系地进行全盘思考与综合研究。这样便可由语言现象的偶然性中发现语言规律的必然性。可贵的是,所有这些不是作空泛的理论性论述,而是根据“桢”、“干”等许多古语词(概念)的引申变化过程来作实证,以解释语言规律。姜亮夫先生曾写道:“最近读到杨公骥先生考证桢干一词的文章,以哲学的观点论证汉语语根的唯物的‘生’的基础与辩证的发展。用这样一个具体材料,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的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学习的文章。”
杨先生1980年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一文。文中,杨先生首先通过周详的考证,说明了《诗经》《周易》和许多古文献中所记述的古人居住的“陶复陶穴”(即“窟穴”、“穹室”、“环堵”)的结构样式:作圆形或方形,半在地表下,半在地表上,壁下部开门户,穹形顶上开有天井(古名“中霤”、“屋漏”)用以通气透光,严冬时可由此出入。这种半地下式的“陶复”地窟,不仅见于古书记载,而且直到19世纪末,仍是吉林、西伯利亚东北部某些民族住室的基本形式。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在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现了这种“陶复”式地窟的古代遗址和后世残存。在黄河流域河北磁山发现的陶复式地窟,经过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794年。由此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古代黄河流域人与东北亚(及阿拉斯加)人便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共同性。进而,杨先生从民族民俗学角度,对两个地区民族的神话祭礼仪式风俗作了精细比较和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如:“冬窟夏庐”、祭中霤、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祭拜月亮、五月祓除祭、逐疫鬼、送瘟神、赛船、挂五色长命缕、辟五毒、投祭物于水中、日月蚀时击盆、逐“天狗”、祭北斗星求长寿、“立尸以祭”(以活人代神或以萨满代神)、雷神执雷斧、祭龙、大傩、方相(萨满装束)、磔狗。这些传统习俗大同而小异,足以证明黄河流域与东北亚有着长期的密切的文化交往与联系。此文由于证据多、论断谨严、见解独到而受到重视。
1980年写就的《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连续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第1、2期。
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把周代视为“奴隶制时代”的权威说法,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根据是否“杀人殉葬”,是否“用人为祭牲”、“杀人祭祀”,是否把人“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是否“贩卖人口”、“人价低于马价”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他引述了马克思区分社会性质、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人身被占有,所以表面看来,奴隶的所有劳动,似乎都是“无偿劳动”,但实际是在“无偿劳动下掩盖着有偿劳动”,因为奴隶主为了使奴隶活下去从事再生产,就必须从奴隶的劳动“所得”中拨出一部分“偿还”给奴隶,作为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农奴从属于领主,在领主的田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三天(即“公田”劳动),再在“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三天”(即“私田”劳动),所以农奴“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作为“雇佣者”从事劳动,做一天给一天工资,“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但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剩余劳动构成了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天才的马克思极其明确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社会经济性质的区别,也为历史分期提出了标准,所以恩格斯说:“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杨公骥据此认为,只有根据剥削形式,也就是根据“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来进行历史阶段分期,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如依此论断,则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占有一小片土地”的,“成家立业”的有自己生产资料的,有“家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所谓“奴隶”,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农奴”。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涉到中国上古史分期的争论,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判断认识周代和先秦社会的性质问题,对先秦的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风俗史的评述等都有重大的影响。杨公骥有理有据的辩驳,是当时国内关于上古历史分期争论中很有分量的一家之言。但是要对郭沫若这样的权威进行挑战,即使论据再充分也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杨公骥先生的批判文章,常常是文字老道、辛辣,好像有些给人不留情面。挑战权威,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杨公骥先生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盲从流俗,不迷信权威,他总是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然后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每提出一个驳论性的观点,都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穷尽式地搜集资料,不只是搜集肯定自己观点的材料,更注意搜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通过客观的比对,然后才得出新的结论,所以他的文章总是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坚持追求学术真理,求实问是,敢为人先,这也是他多年来为学生所树立的榜样。
杨公骥自述
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开始编写于1948年。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另创格局。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承认、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同样角度,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此为杨公骥先生195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论文。“巾舞”又名“公莫舞”,原是汉代的歌舞古辞,共308字。但由于“声、辞杂写”,自“江左以来”已“讹异不可解”,换言之,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已无人通晓。经杨先生逐字逐句地反复考辨,分别词类加以句读,于是巾舞歌辞的本辞、复唱、叹词、和声与标示角色、舞法、舞步、手势的字句便由混缀成一片的文字中分离出来,从而呈现出汉时巾舞的原貌:是表演“母子离别”情景的。1985年,杨先生对旧文作了增订,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的题目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公莫舞》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破译的最早的歌舞剧,因此在文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界,被广泛重视。
此书出版于1962年。所谓“唐代民歌”是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从《敦煌缀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的,共选二十八篇。杨先生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索出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如果根据内容考证年代,则最早的民歌作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至九年(621-626年),有些篇作于太宗、高宗、武后时代,最晚是作于玄宗天宝中期(750年前后)。时间跨度约为130年,显然非出一手。这些民歌(今查出托名王梵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关于“变文”,经多方考证,杨先生认为“变”("变相")乃是寺院的壁画或画卷,所谓“变文”就是图文,乃是解说“变”(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韵文)合组文体的承袭。杨先生除引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所谓“变”(图画)和“变文”(图文)乃是继承我国古代“图、传、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题韵文的“诗”,这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在1978年发表的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干》(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2期)中,杨先生运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依靠文字解说语言,不根据字形考据字义,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也就是将语言现象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心理反射、思维活动、认识过程相联系地进行全盘思考与综合研究。这样便可由语言现象的偶然性中发现语言规律的必然性。可贵的是,所有这些不是作空泛的理论性论述,而是根据“桢”、“干”等许多古语词(概念)的引申变化过程来作实证,以解释语言规律。姜亮夫先生曾写道:“最近读到杨公骥先生考证桢干一词的文章,以哲学的观点论证汉语语根的唯物的‘生’的基础与辩证的发展。用这样一个具体材料,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的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学习的文章。”
杨先生1980年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一文。文中,杨先生首先通过周详的考证,说明了《诗经》《周易》和许多古文献中所记述的古人居住的“陶复陶穴”(即“窟穴”、“穹室”、“环堵”)的结构样式:作圆形或方形,半在地表下,半在地表上,壁下部开门户,穹形顶上开有天井(古名“中霤”、“屋漏”)用以通气透光,严冬时可由此出入。这种半地下式的“陶复”地窟,不仅见于古书记载,而且直到19世纪末,仍是吉林、西伯利亚东北部某些民族住室的基本形式。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在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现了这种“陶复”式地窟的古代遗址和后世残存。在黄河流域河北磁山发现的陶复式地窟,经过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794年。由此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古代黄河流域人与东北亚(及阿拉斯加)人便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共同性。进而,杨先生从民族民俗学角度,对两个地区民族的神话祭礼仪式风俗作了精细比较和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如:“冬窟夏庐”、祭中霤、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祭拜月亮、五月祓除祭、逐疫鬼、送瘟神、赛船、挂五色长命缕、辟五毒、投祭物于水中、日月蚀时击盆、逐“天狗”、祭北斗星求长寿、“立尸以祭”(以活人代神或以萨满代神)、雷神执雷斧、祭龙、大傩、方相(萨满装束)、磔狗。这些传统习俗大同而小异,足以证明黄河流域与东北亚有着长期的密切的文化交往与联系。此文由于证据多、论断谨严、见解独到而受到重视。
1980年写就的《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连续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第1、2期。
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把周代视为“奴隶制时代”的权威说法,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根据是否“杀人殉葬”,是否“用人为祭牲”、“杀人祭祀”,是否把人“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是否“贩卖人口”、“人价低于马价”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他引述了马克思区分社会性质、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人身被占有,所以表面看来,奴隶的所有劳动,似乎都是“无偿劳动”,但实际是在“无偿劳动下掩盖着有偿劳动”,因为奴隶主为了使奴隶活下去从事再生产,就必须从奴隶的劳动“所得”中拨出一部分“偿还”给奴隶,作为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农奴从属于领主,在领主的田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三天(即“公田”劳动),再在“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三天”(即“私田”劳动),所以农奴“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作为“雇佣者”从事劳动,做一天给一天工资,“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但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剩余劳动构成了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天才的马克思极其明确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社会经济性质的区别,也为历史分期提出了标准,所以恩格斯说:“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杨公骥据此认为,只有根据剥削形式,也就是根据“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来进行历史阶段分期,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如依此论断,则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占有一小片土地”的,“成家立业”的有自己生产资料的,有“家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所谓“奴隶”,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农奴”。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涉到中国上古史分期的争论,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判断认识周代和先秦社会的性质问题,对先秦的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风俗史的评述等都有重大的影响。杨公骥有理有据的辩驳,是当时国内关于上古历史分期争论中很有分量的一家之言。但是要对郭沫若这样的权威进行挑战,即使论据再充分也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杨公骥先生的批判文章,常常是文字老道、辛辣,好像有些给人不留情面。挑战权威,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杨公骥先生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盲从流俗,不迷信权威,他总是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然后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每提出一个驳论性的观点,都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穷尽式地搜集资料,不只是搜集肯定自己观点的材料,更注意搜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通过客观的比对,然后才得出新的结论,所以他的文章总是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坚持追求学术真理,求实问是,敢为人先,这也是他多年来为学生所树立的榜样。
杨公骥指导的博士
此书为杨公骥先生讲授先秦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开始编写于1948年。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51年写到第三稿,经中央教育部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有以下优点:如“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至1957年写至第七稿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公骥先生的这本讲义不仅在观点上有创见,而且在体例上革故鼎新,另创格局。例如,在此之前,一般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是从来不研究所谓“原始文学”的,正是从杨公骥先生开始,才在讲义中把“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
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首先探讨了诗(亦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的古文献,详述了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的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二节拍和尾韵所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的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并辩证地说明,正是诗节奏对诗语言的约束,才推动着人们对语言的提炼和修辞,从而促进形象思维和艺术语言的提高和发展。最后阐明原始诗歌在当时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是由于人们的欲求、心理共鸣和条件反射所造成。以上论据为前人所未引,论点为前人所未言。
其次,对中国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首先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所有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只言片语,然后将之缀集成篇,加以口译。这样便整理出一些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古代神话故事。据此,便可对中国原始神话的形成、特点、发展、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精辟分析。杨先生所用的辑佚缀集的方法以后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使用。
与当时流行的观念相反,杨先生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因此在“中国原始文学”专编中设专章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并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进而分节论述了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祭社稷(土、谷)神的祭歌《载芟》、《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和赞美英雄祖先的颂歌《公刘》和《緜》。上引五篇诗歌选自《诗经》。近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认为《诗经》中的诗歌全部为周诗。但杨先生通过精细训诂和审慎考证,运用“自证法”证明这五篇诗歌乃是周族原始时代用于宗教祭祀的祭歌和赞颂诗。由于宗教本身具有顽固的保守性,所以被保留在古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杨先生的考证和论断,已被许多学者承认、袭用。
在讲义中,杨先生设“殷商文学”专编,分章分节论述了殷商时代的文化、工艺、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诗)、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这是以往一般文学是所未涉及的。为了考索商代的音乐和舞蹈,除搜集文献记载外外,杨先生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有关史料,可见工程之巨。同时,由于近世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商颂》不是作于商代,而是周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但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先生为澄清此问题,作《<商颂>考》。文中不回避认为《商颂》作于周代的学者提出的主要证据,逐个根据可信史料作了辩驳。
在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对周礼教的特征,周诗的结集、分类和四家诗说以及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与样式、艺术价值等问题,都作出了独到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庸俗文学”而受到轻视或忽视,这几乎已成为定论。但杨先生一反此说,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实事求是地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出公允评价。在讲义中,杨先生重点分析了《诗经》诗三十四篇,其中“雅诗”就有十四篇,可见对“雅诗”的重视。杨先生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的文学理论,破除了以往传统对“雅诗”和“颂诗”的偏见。
在论“战国时代的文学”时,杨先生开设专章论列战国时在文化方面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辉煌成就,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第一次阐明《乐记》中的“朴素唯物论的命题”和“辩证因素”,并指出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杨先生设立专章分别探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从艺术角度,也就是以文学形象性的有无和大小为标准,来探讨先秦诸子的著作。于是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中摘选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散文来分析研究,从而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性格化的语言都生动的呈现出来。同样角度,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形象化人物、性格化语言、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论述,这样就开拓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据此使人认识到先秦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以往大多把它当做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先生却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以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
1958年完成的论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生平》作为附录收入1980年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多年来,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评述。杨先生在此文中认为这种观点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既不符合历史实情,又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活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之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是相同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一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做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文中杨先生通过史实反驳了唯心主义史学观,并对屈原的形象作了分析。
此为杨公骥先生195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论文。“巾舞”又名“公莫舞”,原是汉代的歌舞古辞,共308字。但由于“声、辞杂写”,自“江左以来”已“讹异不可解”,换言之,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已无人通晓。经杨先生逐字逐句地反复考辨,分别词类加以句读,于是巾舞歌辞的本辞、复唱、叹词、和声与标示角色、舞法、舞步、手势的字句便由混缀成一片的文字中分离出来,从而呈现出汉时巾舞的原貌:是表演“母子离别”情景的。1985年,杨先生对旧文作了增订,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的题目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公莫舞》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破译的最早的歌舞剧,因此在文学、民间文学和戏剧界,被广泛重视。
此书出版于1962年。所谓“唐代民歌”是杨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从《敦煌缀琐》的“五言白话诗”中选出的,共选二十八篇。杨先生使用全部唐代文献为这些民歌作出考证和注释,由此勾索出府兵、贫雇农、逃户、地主、官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后娘、男女二流子各色人等的生活形象。如果根据内容考证年代,则最早的民歌作于唐高祖武德四年至九年(621-626年),有些篇作于太宗、高宗、武后时代,最晚是作于玄宗天宝中期(750年前后)。时间跨度约为130年,显然非出一手。这些民歌(今查出托名王梵志)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关于“变文”,经多方考证,杨先生认为“变”("变相")乃是寺院的壁画或画卷,所谓“变文”就是图文,乃是解说“变”(图画)中情节或景物的说明文。“变文”之所以使用散文、韵文合组的形式,乃是对我国古代“传”(散文)“赞”(韵文)合组文体的承袭。杨先生除引汉刘向《列女图传赞》和武梁祠石刻作证外,还从敦煌变文本身找到众多例证。由此证明所谓“变”(图画)和“变文”(图文)乃是继承我国古代“图、传、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成。至今在国画上还书写散文的“序”,题韵文的“诗”,这是这一传统的余绪。
在1978年发表的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干》(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2期)中,杨先生运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依靠文字解说语言,不根据字形考据字义,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也就是将语言现象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心理反射、思维活动、认识过程相联系地进行全盘思考与综合研究。这样便可由语言现象的偶然性中发现语言规律的必然性。可贵的是,所有这些不是作空泛的理论性论述,而是根据“桢”、“干”等许多古语词(概念)的引申变化过程来作实证,以解释语言规律。姜亮夫先生曾写道:“最近读到杨公骥先生考证桢干一词的文章,以哲学的观点论证汉语语根的唯物的‘生’的基础与辩证的发展。用这样一个具体材料,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的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学习的文章。”
杨先生1980年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一文。文中,杨先生首先通过周详的考证,说明了《诗经》《周易》和许多古文献中所记述的古人居住的“陶复陶穴”(即“窟穴”、“穹室”、“环堵”)的结构样式:作圆形或方形,半在地表下,半在地表上,壁下部开门户,穹形顶上开有天井(古名“中霤”、“屋漏”)用以通气透光,严冬时可由此出入。这种半地下式的“陶复”地窟,不仅见于古书记载,而且直到19世纪末,仍是吉林、西伯利亚东北部某些民族住室的基本形式。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在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现了这种“陶复”式地窟的古代遗址和后世残存。在黄河流域河北磁山发现的陶复式地窟,经过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5-公元前5794年。由此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古代黄河流域人与东北亚(及阿拉斯加)人便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共同性。进而,杨先生从民族民俗学角度,对两个地区民族的神话祭礼仪式风俗作了精细比较和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如:“冬窟夏庐”、祭中霤、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祭拜月亮、五月祓除祭、逐疫鬼、送瘟神、赛船、挂五色长命缕、辟五毒、投祭物于水中、日月蚀时击盆、逐“天狗”、祭北斗星求长寿、“立尸以祭”(以活人代神或以萨满代神)、雷神执雷斧、祭龙、大傩、方相(萨满装束)、磔狗。这些传统习俗大同而小异,足以证明黄河流域与东北亚有着长期的密切的文化交往与联系。此文由于证据多、论断谨严、见解独到而受到重视。
1980年写就的《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连续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1982年第1、2期。
杨公骥先生在文中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把周代视为“奴隶制时代”的权威说法,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根据是否“杀人殉葬”,是否“用人为祭牲”、“杀人祭祀”,是否把人“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是否“贩卖人口”、“人价低于马价”等现象作为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他引述了马克思区分社会性质、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人身被占有,所以表面看来,奴隶的所有劳动,似乎都是“无偿劳动”,但实际是在“无偿劳动下掩盖着有偿劳动”,因为奴隶主为了使奴隶活下去从事再生产,就必须从奴隶的劳动“所得”中拨出一部分“偿还”给奴隶,作为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农奴从属于领主,在领主的田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三天(即“公田”劳动),再在“分给他使用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三天”(即“私田”劳动),所以农奴“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显然分开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作为“雇佣者”从事劳动,做一天给一天工资,“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但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剩余劳动构成了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天才的马克思极其明确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社会经济性质的区别,也为历史分期提出了标准,所以恩格斯说:“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杨公骥据此认为,只有根据剥削形式,也就是根据“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的不同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来进行历史阶段分期,才是唯一科学的标准。如依此论断,则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占有一小片土地”的,“成家立业”的有自己生产资料的,有“家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所谓“奴隶”,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农奴”。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关涉到中国上古史分期的争论,而且涉及到应该如何判断认识周代和先秦社会的性质问题,对先秦的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风俗史的评述等都有重大的影响。杨公骥有理有据的辩驳,是当时国内关于上古历史分期争论中很有分量的一家之言。但是要对郭沫若这样的权威进行挑战,即使论据再充分也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
杨公骥先生的批判文章,常常是文字老道、辛辣,好像有些给人不留情面。挑战权威,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杨公骥先生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他从来不盲从流俗,不迷信权威,他总是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别人的观点,然后才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每提出一个驳论性的观点,都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认真的研究,穷尽式地搜集资料,不只是搜集肯定自己观点的材料,更注意搜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通过客观的比对,然后才得出新的结论,所以他的文章总是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力量。坚持追求学术真理,求实问是,敢为人先,这也是他多年来为学生所树立的榜样。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