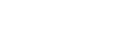熙宁八年的饥疫不限于杭州府,还包括嘉兴府、湖州府在内,可以说两浙路有一半的地区遭到了此次饥疫的袭击。另外,此次疫情与沈起、张靓等地方官员重视不够,救济方式不当有关,如把大量难民聚集起来,发搿救济。
难民本身就是疾疫的易感人群,大量聚集致使环境恶化、加速了疫病传染的机率,所以饥疫流行也是情理之中。最终导致了一城郭萧条,田野邱墟,两税课利皆失其旧”的结局。
所以,熙宁年阊,浙西饥疫,既是天灾,也不乏人祸。十六年后,同样是在杭州,同样是面临饥疫困扰:“岁适水潦,饥疫相仍……”身为郡守的苏轼吸取前一次渗瘸教训,及时采取了比较妥当的救济方式和严格的隔离措施:第一步减免赋税,减轻灾民负担,稳定疫区人心。
具体做法是“请于朝得减上供米三之一”;第二步实施救济,利用朝廷所赐300道度牒(国家发给僧尼的免税凭证)广泛发动僧尼救济疫民,发挥地方的协调功能“益市粟济饥殍,明年贱粜常平米,又作糜粥遗人”,以解决疫民生存问题;
第三步建立安乐坊,隔离病人,并“命医官分治”,赖以全活者甚众。…在减赋、度牒、贱粜、医治等措施的相互配合下,饥荒所造成的疫情得到缓解,传染范围得到控制,疫民的生存和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疫区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从而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救治效果。
展开全文
说明只要采取比较科学合理的救治措施,是能控制疾疫的爆发和蔓延的。北宋灭亡后,宋朝统治中心移至江南,江南人口大增,加之气候异常等因素,因此,江南疾疫流行无论规模还是频率均比北宋为多,典型的当属庆元元年两浙疾疫。
庆元元年(1195年),两浙疾疫疫情出现是在庆元元年三月的临安。此次疾疫无论染疫人数、疫期、疫区均比熙宁八年浙西饥疫更为严重,当属重度疫情无疑。从疫期看,自三月至六月疫情不断蔓延,断断续续达三年之久方逐渐平息:
从疫区看,庆元疫情最初流行于临安府,而后由于临安发达的水陆交通。,频繁流动的人口,使疫情迅速向周边扩散,蔓延至两浙绝大多数府、州、县,如浙西的湖州、秀州、常州、润州,浙东的庆元、绍兴等地,从春天开始到夏天一直受疾疫困扰,情形十分惨烈。
这种扩散式的疾疫几乎囊括了整个两浙路,范围之广、疫情之重,均胜以往。尽管朝廷和民间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包括给钱、发药、差官安抚、助葬等,结果旅然令人触目:晾心。
当时湖州府是染疫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文献记载,有一个村庄的七百户人家,有近一半成为绝户;常州疫情不逊湖州,“民病者十室而九”。嘉兴城内更是“日毙百余人”,可见疫情蔓延之快,死亡人数之多。由此而知,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一次烈性传染性疾疫,
而且估计朝廷对此次疫情尚无特别有效的控制办法。当然,两浙地方官员仍然在努力救治,两浙运副沈诜向朝廷提出三条建议:一是请求朝廷降度牒五百道下本司或提举司,并转分给府下各州县,各地可根据饥疫轻重程度,逐一“拔下逐州委官分任其事。”
特别强调朝廷在疾疫救治过程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同时为调动地方官员救灾的积极性,还把救灾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事毕,考验区磨,以全活人数多寡,旌别闻奏,优与推赏。”
加强隔离救治:“州县合选委明脉医官,各分坊、巷、乡、保医治,其合用药材于所委官从实支给,仍日支食钱五百文,其有全家患疾无人煎煮者,选募僧行管干,每日亦支食钱三百文,并各置历抄记全活人数。”
对老弱孤独残患流离道路者,州县要安排空闲房屋或庙宇供他们暂时居住,对被遗弃的孤儿,“募人养之,官为记号月”三是继续赈粜,抑制物价大幅上涨,打击囤积居奇的商贩等,“如有藏匿,许人陈首”。以上建议可视为地方官员面对疾疫的应对手段。
沈诜向朝廷报告后,朝廷“诏令礼部降度牒五十道付沈诜”。瘟疫是多发于春夏并与当时气候环境有关的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在气候异常之时,除温病外的其他各类传染病也容易出现。气候异常,引发疾疫的可能性增大。
在宋代因气候因素引发的疾疫不少,如“淳化三年(992年)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瞑,雷震有倾乃止。先是都下太热,疫死者众,及此风至疾疫遂止。”嘉定二年(1209年)“都民疫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于暑并,多疫死”。
地理环境,江南的地理特征对疾疫流行也有一些影响。其一,江南湖泊众多,河流纵横,降雨丰富且集中,自古以来有“水乡泽国”之称;特别是地处江南核心地带的太湖流域,更是沼泽密布、河港纵横,大小水系达200多条。
地势低洼,易于发生洪涝灾害。太湖流域洪涝灾害比别处多。浙江共75座城市,其中有55座城址在0—200米高度,占73%,仅有7%的城址在200—400高度。如临安、湖州、秀州、常州、其疾疫的爆发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大灾之后,特别是水灾、旱灾和地震过后,许多人往往无家可归,被迫流落异地,造成痢疾、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流行,有时灾后死亡人口甚至超过始发灾难。所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比如,熙宁中浙西饥疫,导致苏州死亡30多万,杭州死亡50多万。这些无不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饥荒有关。
水灾,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江南地区尤甚。就《宋史》所列宋代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共有1219次,而水灾即达到465次,占总数的38%,可见宋代有三分之一的自然灾害属于水灾。
尽管不是所有的水灾都会引发疾疫,但就江南而言,其地势低洼,又有长江、钱塘江、江南河、太湖、鄱阳湖等诸多大小水系,从而构成南北纵横的水网。在江南多雨的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水灾引发疾疫的可能性相对比其他地区多。
如两浙路所辖七州,除严州(治建德县)外,苏州、润州、杭州、秀州、湖卅I、常州等六州皆靠近太湖。一旦太湖发生水灾,对周边的府县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实际上,如前所说,宋代太湖流域在宋代三百多年时间里共有涝灾55次,平均6年左右一次。
如仍以浙江为例,则大致每10次水灾就有可能引发1.3次疾疫。水灾频度越高,规模越大,时间越长,其带来的生产的破坏程度越高,死亡人数越多,导致疾疫的可能性自然就越大。如果仍以浙江为例,旱灾引发的疾疫比例通常占1896左右。
有时旱灾的影响往往延续到第二年或第三年。这在灾难史上称为灾难继发性特征,即一种灾难往往可能诱发一种或数种其他灾难的发生,而且继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危害有时甚至大大超过原发灾难,从而呈现放大效应,洪灾后的传染病、旱灾后的饥荒、疾疫均属于此类情况。
虫灾、地震等因素,宋代的疾疫灾害中近4%是由虫灾和地震引发。其中蝗灾是虫灾中最常见和后果最严重的灾害之一,“伏见今岁江东九郡大旱者士加以飞蝗,所过遗孽,蔽江盈野,其积数尺,草木芦苇为之一空……”。
其他的虫灾诸如蝻灾和螈灾o,都可能对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江南地区的湿地气候,特别适宜于蝗虫的生长和繁殖。这样一来,江南地区的蝗灾自然比其他地区严重。另外江南地区严重的旱灾,也容易导致蝗灾。
研究表明,历史上蝗灾滋生旱蝗二灾的相关系数为0.9150,扩散区为0.8260。所以,正如苏轼所说:“从来旱蝗必相资,此事我闻老农言。”蝗灾之后的饥荒和流民问题成为引发疾疫的重要因素。
如“隆兴元年(1163年)八月,江浙飞蝗蔽天日,害稼。”八月正是庄稼快要收获的金秋时节,而在这种时候出现蝗灾,对农业无疑是灾难性后果。然而正是这一年,江浙先是大旱,接着又是大风雨害稼。
第二年,即“隆兴二年(1164年),浙西大雨害稼,湖、秀大水浸城郭、坏庐圩田……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浙之饥民疫之甚众。”可见虫灾是引发疾疫的重要因素。地震是一种突发式的破坏惨烈的自然灾害,地震过后,因大量人畜死亡、环境破坏同样也可能引发疾疫。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淮南地震,三年(1000年)江南地震。”。绍兴六年(1136年)地震,七年(1]37年)建康大疫。这并非巧合。固实际上,地震引发疾疫是与地震造成大量人畜死亡和环境破坏有关。地震一旦发生,顷刻间房屋倒塌,人畜死亡。
如景祜四年(1037年)忻州地震死亡10742人,受伤5655人,各类牲畜死亡50000头。大量人畜尸体假如不能得到及时掩埋,往往成为细菌繁殖的寄体,极易引发疾疫。
所以,对各种突发灾害中出现的大量尸体的处理,宋朝朝廷比较重视,不仅设立漏泽园,由朝廷出面组织掩埋无主尸体,还出钱帮助一些人家掩埋尸体。同时还对受伤民众实施医疗和生活救济,鼓励民间各类人士参与震后救治,如对掩埋200具尸体的人,奖励度牒一道。这对抑制疾疫流行是有一定效果的。
饥荒,宋代江南地区所爆发的流行病,不少因饥荒引发。这大概是灾害后,粮食收成锐减,物价腾贵“斗米百钱”或“斗米千钱”,朝廷依然征收重税或救灾不力、或救济方式不当造成。假如仍以浙江为例,饥荒致疫大致占总疾疫量的27%左右,在所有引发疾疫的因素中比重最大。
宋代饥荒之严重缘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引发饥荒的水旱灾害具有普遍性、继发性、突发性等特点,几乎达到无时不灾,无处不害的地步。其次,江南大多数地方人的数量和密度过大也会造成粮食供应不足而致饥荒。
比如杭州,苏轼就曾说过,“杭州自来土产米谷不多,全仰苏、湖、秀等州搬运斛斗接济,若数州不熟,即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的确杭州自来地狭人稠,经济发达,战乱时期四方之民更是云集于此,一有天灾,发生饥荒的机率远胜它处,疾疫发生的频率自然也不会低。
饥荒,本属自然灾害,假如朝廷不能有效控制,则很快会从自然灾害演变为人为祸患。灾害历史学认为“饥荒的实质是以粮食生产崩溃为核心的社会灾难,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则是农业时代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的重心所在。”
因此,国家对百姓的剥夺过重,不仅加重饥荒程度,还会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宋朝对百姓盘剥之甚.正如朱熹所言,古之刻薄之法,本朝均有。由于苛税太重,致使大多地方“郡无一年之蓄,左无累月之财,民间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