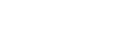崔颢是唐代著名诗人,崔颢以才名著称,好饮酒和赌博,与女性的艳情故事常为时论所薄。早年为诗,情志浮艳。后来游览山川,经历边塞,精神视野大开,风格一变而为雄浑自然。《黄鹤楼》一诗,据说李白为之搁笔,曾有“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赞叹。
崔颢,唐代诗人,与李白生于同一个时代。当崔颢开始写诗时,彼时大唐诗坛已是群星璀璨,执牛耳者当属仙圣李杜;王勃一篇序言已经被放到初唐的压轴位置;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留下了怆然的泪痕;贺知章满载荣誉在百官相送下已经告老还乡;同龄人中,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也成了“边塞四大天王”,豪气冲天,气盖河山;王孟二人醉心山水田园,专攻小调,也被世人传唱。
万众写诗的年代,在李杜这样的标杆下,全面超越几乎没有可能,可就算在方寸之间胜过一招半式,也算永垂不朽了,崔颢就是这样一个诗人。史料记载,崔颢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这样的转变或许并不奇怪,人总是这样,在经历无常的人生历练之后,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醒悟,达到一个新的意识境界。
崔颢便是如此,少年成名,宦海浮沉多年终不得志,二十年间,游历大江南北,随着对自然风情的不断领悟,对自我的认识也不断升华,而最终一改往日颓靡,诗风大振,激昂豪放,气势宏伟,更是凭着一首《黄鹤楼》名扬天下,竟让太白观而搁笔几度模仿,被后世传为佳话。
暂不论品行,单从诗作来看,崔颢的一生是有着一道明确的分界线,分界线前,多写闺乐,纵情迷性;分界线后,雄浑奔放,说尽戎旅。一位诗人的创作风格取决于自身三观的呈现,或许这条分界线正是崔颢的一场顿悟,也是他趋近成熟的人生观。
少年为诗,及冠中第辉煌一时
崔颢年少聪慧,少而能诗,十多岁时便可写得一手好诗,可他写的诗,却被时人所不齿:颢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崔颢流传诗作四十余首,写妇女闺情的有十五首,细细读上几首便可知道,以“浮艳”而论实在有过其实,至少还有很多诗,内容健康向上,在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遇到被君王冷落的女人,他写《长门怨》:君王宠初歇,弃妾长门宫。泣尽无人问,容华落镜中。遇到沦落风尘的失足女,他写《邯郸宫人怨》:邯郸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见一妇人。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十三兄弟教诗书,十五青楼学歌舞。...
比起轻薄浮艳的少年郎,这些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像是一个“妇女之友”的形象。不仅有写贵妇的,崔颢的笔下还有贫民女子:川上女,晚妆鲜,日落青渚试轻楫。汀长花满正回船,暮来浪起风转紧。自言此去横塘近,绿江无伴夜独行,独行心绪愁无尽。
崔颢早期的这些诗多以女性视角,在一个男权的社会,或许是很容易引起非议的,可他的诗中也不乏政治抱负和忧国情怀:妾年初二八,家住洛桥头。玉户临驰道,朱门近御沟。使君何假问,夫婿大长秋。女弟新承宠,诸兄近拜侯。春生百子殿,花发五城楼。出入千门里,年年乐未休。字里行间都在影射当朝权贵,针砭时弊,暗藏讥讽。
当然,对于崔颢的诗,当时也有不少正面中肯的评价,极富诗名的崔颢在二十岁前后赴长安应试,一举高中,鲜衣怒马,辉煌一时。
声名狼藉,无人引荐仕途无望
二十岁前后便能考中进士,无可置疑,崔颢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人在仕途场上不至于混个碌碌无名的下场,而崔颢为官多年,事业上竟毫无起色,其原因也不过是在早年间,因为一首诗而落了一个“小儿无礼”的名声。当时崔颢名声渐起,超级大咖李邕听说之后,便邀请这位青年才俊到家里一叙。《旧唐书》本传里说:邕素负美名......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
这样的一个超级公知主动约见,对于崔颢来说,是一个可以入仕扬名的绝好机会,见到偶像,崔颢虔诚地奉上自己的诗集,头一首诗就是这首《王家少妇》。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十五岁嫁给美男子王昌,步履盈盈走入华美堂室。自负着青春年少,将此生幸福全全寄托给夫婿。婚后,两人歌舞吟唱,竟采花草,幸福赛神仙。
以美人出嫁来比喻知音赏识,古已有之。崔颢将李邕,比作是那个大众男神王昌,而他自己,就是那个登堂入室,独占男神的十五岁少女。狂妄而直接,让人啧舌,无怪乎李邕看了第一句就大怒,呵斥崔颢“小儿无礼”,转身就走。这之后,崔颢更是声名狼藉,无人举荐,仕途上基本晋升无望。
辞官漫游,二十年间风尘苦旅
非议日愈增多,这世道已然容不下崔颢,他毫不留恋,辞官出走江湖,这一走,便是二十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节点,崔颢将自己置身于风尘苦旅之中。这20年间他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从江淮到东北,边关塞北一路走来,诗路也随着旅程变得开阔而雄伟: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热情洋溢,大气凛然,再不见闺情诗身影了。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雁门胡人,家住在代郡之地,以打猎、耕作为生。冬天山上寒冷,他就放把野火取暖。下雨时山上湿气蔓延,就且做烟雾缭绕。天下太平,辽西也不再打仗,报国赴难的机会也没有了,还是把自己灌醉吧。
孤独自处,逍遥自在,饮酒自醉,或许才是崔颢最深的向往吧。游历天下,唯有这慷慨雄浑的边境风光,金戈铁马的快意生活,才最让人留恋。当崔颢写下这些凛然风骨的边塞诗时,崔颢已经开始改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写小情小爱的无礼小儿。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
变与不变,早已没有意义。年轻时的情怨缠绵,中年时的凛然风骨,都是最崔颢最本真的模样。也许,这真的应了那句话:“诗穷而后工”,当崔颢完成了少年轻薄到中年困顿,直到老年的刚劲的旅程时,他才真正跳出狭隘的轻薄浮艳,重新体会人生这趟单向的旅程。
人生顿悟,黄鹤楼上名篇盖世
而他真正的转变则是从那一次偶然登临黄鹤楼开始,远处落霞映日,江上烟波腾起,仙人驾鹤而去已不论真假,崔颢的脑海里突然间闪过一道灵光,诗歌最隐秘最精深的大门赫然开启,这一刻,他顿悟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仙人一去不返,留下危楼高耸,白云翻飞,此时的崔颢,站在这黄鹤楼上,极目远眺。晴朗天空下,平原每一棵树都历历可数,鹦鹉洲上,芳草茂盛绵延千里。芳草萋萋,一缕乡愁踏水而来,眼看着日薄西山,羁鸟归林,池鱼回渊,这浩浩烟波,渺茫一片,崔颢终于意识到,流离半生的追逐和逃避,最后,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游子。每个人都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在滚滚浊世中,到处都是难行的路途。也许在这一刻,面对着无限的江山,面对着悠远的时空,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年少的辉煌与半生的失意交织在胸,纠缠不清,形成了万吨沉埋地底,但是一遇缝隙就会喷薄而出的岩浆,而登临黄鹤楼,就为这岩浆寻到了这难得的缝隙。于是,当诗人的沉郁冲开缝隙冲向云霄的时候,诗人就再也不顾及什么平仄格律之类的清规戒律,而任由这郁结之气挥洒恣肆了。这篇黄鹤楼,前一句平铺直叙,当黄鹤二字第三次出现,立即奔流而下。全诗大气深沉,前有浮声,后有彻响,堪称完美。
而他的这首诗,终于在崔颢对自我认知的升华中,登上了唐朝律诗的巅峰。以至于后来,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竟然捶胸顿足,自愧不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心中郁闷,可想而知。离开黄鹤楼的李白,一直难以释怀,于是,写了《鹦鹉洲》: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与崔颢《黄鹤楼》如出一辙,嫌不完美,又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仙太白,竟然也有仿写他人诗句的时候,不仅李白模仿,此后的1000多年里,模仿者众多,还包括鲁迅。但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功名心切,重回长安客死他乡
漫游过后的崔颢已经年近半百,多年的漂泊,应该催生出更浓的归乡情绪,可崔颢,却并非如此,相反,他越发的急求功名,这应该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士子的执拗,天宝年间,崔颢回到长安,做起了京官,官至司勋员外郎,和二十多年前一样,一个小官职而已。754年,崔颢客死长安,未得返回故里。
崔颢这一生,就是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反复的挣扎和解脱。而那首《黄鹤楼》,则是他一生的浓缩体现。他的愁既有报国无门、功业无成的无奈,又有怀才不遇的忧伤,人生短暂的迷惘,更有游子迁客思念故土的乡愁,这种愁,如江雾般萦绕于诗人的心头,挥之不去。而崔颢的忧愤哀怨随着时间的推移、景致的转换发生了转移,诗的寄意急转直下,由壮志难酬的悲壮转而为遁世归乡的悲凉。
是啊,归乡是唯一的出口,可崔颢为何在半百之后特别是在漫游归来,却仍然选择跻身于功名场?或许是因为一展抱负的倔强,但我想,更多的应是为之前所受到的批评、误解、指责和诋毁,所表现出的不甘心!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久伴学 9banxue.com】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